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里面,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曾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出他对爱情的理解,那句话被表述得非常美,它超乎想像的柔软和甜蜜让我迄今熟稔于心: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我生命的某一时刻我也经历过这些。然而我已记不得这些。我所记得的是,爱是以另一个男人的形式,带着新的希望,新的梦想重回我心中。
科埃略是善意的,但他不曾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男性的方式说话,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爱情的消逝决非那么简单一件事:失去,一定意味着无法重回,因为它已经导致了生命中某部分柔软组织的死亡。在这点上,以色列女作家茨鲁娅·沙莱夫的《爱情生活》显然更加贴近和具有说服力。这本读起来简直具有压倒式窒息感的小说,叙说了已婚希伯莱年轻女子伊埃拉被父亲的旧友、母亲的旧情人阿耶厄所吸引,一步步脱离自己正常的婚姻、生活轨道,为情欲和幻想所左右,最后失去一切的故事。它让人感到绝望之处,在于伊埃拉是怀着对爱的热望去追寻这份感情的,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阿耶厄只不过是个不再对任何女人担负心灵责任的老花花公子。其实,这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崩溃的预兆,冷漠而粗砺,甚至是肮脏,文字中暗暗流动着从《圣经》中借来的“圣殿被毁”的意象,作者运用了大段直白也并不优美的性描写,来营造女主角无法摆脱的屈辱感,因而引来不少评论家非议。
为什么伊埃拉会沉迷于这样一种所谓“爱情”无法自拔?这和她自身的弱点不可分。女人对现实感到失望或不满足,就会开始寄望于幻想中的东西。她们为自己打造了美妙的爱情圣殿,一厢情愿要它尽善尽美,哪怕发现和期待不那么相符合,也会用一个个借口来打发疑惑保持信念。所以,阿耶厄的出现不是偶然却是必然,被他伤害更像一种宿命。当然,也是教训。而最后被那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从床上赶走时,伊埃拉终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明白过来“他是在依赖我对他的依赖”。

古往今来的女人都很难对此保持清醒,即使写下《第二性》的波伏瓦,也从来没有摆脱过萨特对她精神上的摧残,她可以在自传里说谎保持强硬,但深夜里独自一人哭泣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老派的英国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实在对此感到不解,他在《知识分子》里面发出天真的质问:为何一个主张女权的人,却在生活里和自己的哲学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说波伏瓦很厉害,厉害到敢于保留那座早就被证明是海市蜃楼的圣殿。她很清楚不能推翻——一旦推翻了你就回不去的,因为它曾经是梦想所在,每每念及便要心碎不已。
《爱情生活》 [以色列]茨鲁娅·沙莱夫 著 周晓苹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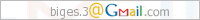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1 条评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难道不走自己的路,别人就不说了吗?
问君能有几多愁?几多呀,到底?我没愁,用不着你问,有愁也不告你。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没不义呀,偶尔还仗义,可我还自闭,咋办?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貌似跟你没太大关系,跟天有关系,天上的事儿,咱就别搀和了。把酒问青天,不就是喝酒么,用的着去问天么?天管着你喝不喝酒,喝不喝高呢?喝酒还得去问天,那酒能喝踏实么?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瞅瞅,喝个破酒,还老跟月亮起腻。干嘛要停杯问呀?必须干杯问!一看酒量就不大。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然是您主沉浮,偶主轻浮。
孔雀东南飞,何不言西北?废话,西北有高楼,直上浮云端。
死了都要爱!真够伟大的,估计是被爱逼死的。
秋水共长天一色。万一秋水被污染,万一长天都是尾气,那还一色么?
留取丹心照汗青。不用留取了,现在汗青这么多,天天在网上跟我说“汗”,多逼烦呀。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惟一的神话!我咋就觉着——你放电,你脱光,你是二逼的废话!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哥们是横眉绝对竖中指,俯首怒撮神户牛。
一种相思,两处离愁。别把我算上,我就让你一种相思,一处离愁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看就是上下班高峰老经过嬉碧递。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就是一破彩虹么,见不见都无所。万一经历风雨经历大发了,还没等彩虹出来,这人就没了,咋办?人那一家老小那保障,你管么?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合着刚掉泪你就擦呀,干哈呀这是,明摆着想让人家擦干一切陪你睡,yueyu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