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6日星期五
亨伯特·亨伯特
最近刚刚看完的一篇小说,王谨的《腐食动物》。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陆陆续续贴过来。关于丁冬说苏东老变态由来的文字,我贴在评论里。
所以,丁冬,无耻的不止你一个,我不鄙视你。你无耻是因为你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知道人应该活得现实一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也没有有权有势的爹妈的人,更要比别人活得现实。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虽然说你我都算有文化的人,也不可否认我们都还算聪明,可你知道什么才叫聪明?我告诉你——用你裤裆里的家伙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浪费脑子,你何必劳动高级中枢?
这就是智慧,兄弟,生存的智慧。
你不能说这是意志消沉。只能说明我们都成熟了。你应该见过我,丁冬,我是你师兄,是你学长。对,就是那年夏天,你不会对我没印象。
那年夏天,我举着一根竹竿,竹竿顶上挑着一个我从解剖教研室偷出来的骷髅头,我肃穆地走在被太阳晒得软乎乎的柏油马路上,气宇轩昂得活像个中世纪的骑士。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但我还是尽可能大声地喊着令旁观者激动的口号,那时我感觉自己很牛逼,我的脑子里是五四先贤,是柔石殷夫是刘和珍君。在我身后,是黑压压的人群,那是我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也许你当时就在人群中间,我领着你们,唱着国际歌,踏着让这个世界战战兢兢的步子前行。
在那场运动中,我惟一的收获是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生。丁冬你还有印象吗?我记得你说过我是老变态,你说有一本书写的就是老变态的故事。我和那个高中女生的故事也能写成一本书了。她后来对我说,她是在我领唱国际歌的时候爱上我的,是在我演讲的时候爱上我的,那时候她站在围观人群的最前排,她跟着我们一起唱歌,唱完之后才发觉自己已是泪流满面。她跟着我们的队伍走到学校,我疲惫不堪,刚进宿舍就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我的舍友好不容易才把我叫醒,说有人找。走廊里靠墙站着一个女孩,小鼻子小嘴小个子,胸前两个若隐若现的小乳房,表明它们的主人正处于发育期。她怯生生地看着我,嗫嚅着说:“你能教我唱国际歌吗?”
复课之后我也没怎么上课,我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女孩子。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只有一张单人床的民房,我买来足够吃一个月的方便面,啤酒和肉罐头鱼罐头,还有一只插电的水壶。白天我躺床上看书睡觉,其他时间用来想她,傍晚她放学后就来到我们的小屋。吃完饭我们就上床,我动作轻柔地一次次进入她的身体,我欣赏着她睫毛的悸动和透明皮肤下一波一波的红潮,我咬着她小巧的耳垂,抚摸着两个正在成长的小乳房,听着她细声细气的呻吟。然后我们在床上吃着东西喝着漂白粉味的白开水,一遍一遍地哼唱着欧仁·鲍狄埃的歌。我给她讲我们的故事,讲发生在首善之区的故事,她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流泪。我夸大了自己在那个大事件中的作为,我把另一些人的思想偷来变成我的思想,这样,我在她的心目中,就越发得忧国忧民,越发得伟大了。她疯狂地迷恋我,不惜逃学来出租屋找我。她第一次把处女的身体交给我的时候,绝不像一般女孩的半推半就,而是坚决地要把自己给我,她说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我哆哆嗦嗦地进入,尽可能轻尽可能柔,像古董商对待一件脆弱的瓷器。
后来?我们的故事没有后来。我是个王八蛋,欠抽,丁冬我求你,给我一拳,也许我会舒服点儿。
有一天她父亲跟踪着女儿进了我们的家,我站在这个温文尔雅,却表情凝重的中年男人面前,她抱着我,背对着她的父亲,准备替我阻挡随时可能袭来的拳脚。我推开她,跟着她父亲走到门外,他说,只要我答应不再见他女儿,他可以不到学校告发我。这是个我想不到的结果,我本来要跪在地上求他,只要不告诉学校,只要不影响我毕业,我可以发誓永远不再见她女儿,如果还不能消气,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把我打个半死。这么低的要求,我毫无困难地答应了。我们回到了屋里,她坐在那张属于我们的床上,见我进屋就飞快站起来,一双清亮湿润的眼睛迅速扫视着我脸上暴力的痕迹,她当然看不到什么。然后她对自己的父亲说了一句特别傻逼的话:“我爱他,他是个斗士,是个爱国者。”
我心里一热,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我还是在她父亲凌厉的眼神“鼓励”之下说:“你大概是傻吧,哪有什么斗士和爱国者,我其实就是爱出风头,逗你玩的话你还当真?”
我说完之后她失语了。只是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那种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啦。
我用仅有的一点力气躲开了她的目光。我听见她父亲拽着她走出了这间屋子,仿佛拖着一件重物。
后来我见过她一次,隔着老远。
毕业那天,我去了她的学校。下课铃响一响,学生们涌出每个教室向校门走来时,我跑的比兔子还快,头也没回。可,我本来是想见她的。可我在人群中准确分辨出她的脸,那张我捧过亲过抚摸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小脸蛋的时候,我怕了,我虚弱了,我身上只剩下逃跑的勇气。
鄙视我吧,兄弟。
我还算顺利地毕业了。我的检讨足够深刻,我送给系主任的礼足够贵重,那是我爹脱了一万块坯、烧了一万块砖赚来的钱。可我的档案中还是出现了这行文字——该生曾参加反革命暴乱,鉴于年少无知兼已作深刻检讨,给予记过处分。
我牛逼过。可如今这只能证明我傻逼过,虽然我谈不上后悔,可你知道吗丁冬,假如没有记录在我档案中的这两行字,以我的成绩和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我会分配到卫生局,也许现在我就是卫生局长。我就会坐着奥迪车到各大医院巡视,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小丑就会列队相迎。可是现状你看到了,那年毕业的所有大学生都不许进机关,我被发配到这个破鸡巴医院里,还得喊一声皇恩浩荡——没给关起来或者开除就不错啦!
这儿的气氛令人窒息,我的主任我的同事都他妈的是贪得无厌的小人,他们的廉耻底线是不主动找病人要红包,他们为了能给病人一个呈上红包的暗示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在这个地方,我闻不到一丝学术气息,看不到任何希望,病房窗户上生锈的铁栅栏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何其相似。我上班的第一年,和一个快要退休的副主任医师在外科门诊面对面枯坐,每天我都打来开水,给他泡好茶,给他拿来当天的报纸,我外表谦恭内心敬仰,我希望这位老主任能把他的经验倾囊而授,我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不能再让另一个梦想破灭,我想成为最好的医生,至少那时,我还坚信治病救人是一份高尚的职业。可是丁冬,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看见老主任桌子上摆着一盒红塔山,我发现烟盒里一根烟都没有,就随手扔到字纸篓里。老主任马上弯腰捡起来,把空烟盒放回原处,他见我一脸疑惑,就跟我讲了空烟盒的秘密,他说苏东你有所不知,这个空烟盒就好比“引蛋”,你是农村来的你应该见过,农村老太太们经常把一个看上去跟鸡蛋没什么两样的空蛋壳摆在鸡窝里,母鸡看见了就会更积极地下蛋。这盒红塔山就是我的“引蛋”,看病的时候我就拿烟盒找烟抽,病人家属一看我没烟了,就会跑出去给我买烟。丁冬,你没见过这个老头,不过你一定能想到他那张脸上,给徒弟介绍经验的得意。说实话我听得都快吐了,可还是不得不摆出一副惊诧和钦佩的面孔,就像武侠小说里得到武学宗师真传的弟子。我的配合让这个老家伙更加得意,他微笑着,继续传授他的“引蛋理论”,他说也难免碰上笨母鸡似的人,“有时候我把烟盒倒过来看,那些笨蛋也没反应。这时候你就丛兜里掏出钱给他们,就说正看病呢脱不开身,让他们帮你到门口买盒烟。一般这种时候,再笨的蛋也能醒过味来,他们哪敢要你的钱?还不赶紧屁颠屁颠地去给你买烟,说不准你就有一整条烟抽呢!”
你瞧,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那张令人作呕的寡廉鲜耻的老脸就是现实。我在老师们的教育下受益匪浅,在这个医院,你不需要追求专业技术,至少先不忙,你的第一课应该是学会对付笨母鸡式的病人,让他们出血来供养你。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老家伙退休之后的一年翻天覆地,假如他现在还坐在门诊,他不会满足于病人一条烟的孝敬,他的“引蛋”也该升级了,要不然岂不是太没追求,太不与时俱进?
丁冬,刘满月母女眼下是不错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不可能让你上到更高的地方,你应该有更高目标的追求。要站,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刚认识你那会儿,我就看着你眼熟,这回对上号了,你就是挑着骷髅头走在最前边的人,你就是在广场上点燃花圈的那个人,你站在高处演讲,激情四溢,你把刽子手说成了筷子手,可即便这样也没有任何人笑,所有的男生女生都无比崇拜地仰视你,你站在火光后面,空气在你四周痛苦地挣扎、扭曲,你好像被密封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之内,好像你的身体也将要融化将要蒸发。你那时候的形象加重了悲剧意味,所有的人都哭了,国际歌唱了不知道多少遍之后,演变成了没有节奏感的哭声。
我的故事很长,比山鲁佐德的故事还长,老刘头的酒很多,足够喝到把我的故事讲完。
你不认识我。我是个小角色,而你是英雄,以一个无畏的殉道者的光辉形象矗立在其他人面前。那时候我就夹在人群中,看着所有的人对你膜拜,被你感染,被你搞得热血沸腾。人群撤离时,你仍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身后是空荡荡的广场,我记得我回头看了一眼,地上都是你的信徒们留下的泪渍和鼻涕,还有一片片飞舞的灰烬,好像黑色的鸟四分五裂的肢体从空中跌落。
这些遗物是你们这些人绝望的象征。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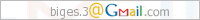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1 条评论:
苏东进来的时候生猛无比。穿的像个直立行走的狗熊,身后跟着他的女朋友。这女孩极小巧,虽然也穿得很厚,但和苏东比起来就像一个会移动的毛绒玩具。女孩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眼中含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我还一个微笑给她,她的小圆鼻头冻得通红。私下里我跟苏东说过他有猥亵幼女的嫌疑,这女孩实在太小了,从身形和面容来看最多有十七八岁。 “那是你看着小,其实都二十一了。”苏东很是得意。
“这姑娘可爱吧,像个大号的毛绒玩具,我在床上抱着她,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苏东补充说明,搂着这个娇小的女孩能激发他的父性,做完爱之后,他常常被怀里温热的小肉体感动得泪水涟涟、周身战栗。我为此做得分析是,“让你激动的不是性快感,是负罪感——接近乱伦的性行为之后产生的负罪感。”那时我还没读过纳博科夫,否则我会说他是亨伯特·亨伯特 ,一个老变态,一树压在嫩海棠上的梨花。苏东没说话,可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血似乎被一个隐藏在皮下的泵抽走了一大半,沉默了半天他说:“也许,你说的有那么点儿道理。”
我怀疑他脸上的血是被某个我所不知道的往事抽走了,我知道不该再就这个问题探讨下去。
负罪感也能衍生出心理上的欣快?也许吧,也许。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