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
我的Les filles
.不是前言的前言
案头书,非诗即词。随手翻去,千百年来化不开的脂粉香沾染在我的手指上,在书页滑过的时候轻轻叹息。
作为文本存在的女性,一直在中国男人的笔下面目模糊,身份暧昧。“唯将长夜终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告诉我们,正室夫人想入情诗,需死得逢时。彼三首《遣悲怀》凄恻缠绵,情真意切——作者趁势纳妾两枚。“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则是诗仙李白出去混之前写来讽刺老婆(活着的)。贞妓(贞!妓!)关盼盼为张愔守节十年,尚有人不吐不快,“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终于被白居易一诗逼死。那个时候,文艺青年们串妓院是去恋爱的;几乎所有的情诗都是写给职业妇女的,而每个女神都是用来意淫的。
木心所言不虚:“古时候的男人...他们真是十分善于写作的。”但现在我想的却不是这些。
我的姑娘。有片言只语在我紧闭的眼睑上舞蹈,有悲欢,有歌哭。丢掉线装书,我打开录音机,一些杂音伴随着往日歌曲唱起。是的,在这里了。
“看着天边的云啊
静静地飘啊飘啊
小河的流水也在轻轻地流淌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
等到你再一次
回到我的身旁
我的姑娘
你总是这样
我的姑娘
我的心为你感伤”
——宽恕《我的姑娘》
简单的四三拍,一四五和弦,反反复复唱着我的姑娘。我看见西华门傍晚的城墙边,有人回眸对我一笑,转身跑开。这与初恋有关,但现在我想的却也不是这些。
我的姑娘,她们在那些我无从忘怀的旋律里长久地“诗意地栖居”着:非歌者,是歌。
——不是前言。姑且写下。给Z,为不会说话的爱情,为阴差阳错的一切。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
看着你飘动着迷人的身体
透出了像花一般的美丽
你想要人世间的痴迷
并不在乎谁会把你丢弃——花儿《花》
有着睡莲一样柔嫩面庞的姑娘,有着丁香一样细密愁怨的姑娘,有着水仙一样悠长脖颈的姑娘,有着百合一样神秘味道的姑娘。她们跟雨一起哭泣,落在地上,睡在雪的怀里。春天来临,她们结出花蕾,在歌声里轻轻地颤抖,伸出修长的手指,触摸那过路的人。在手掌中怒放的姑娘,过了一夜就凋零,但无人在意。
这是一九九九年,年轻的花儿乐队歌颂着花。而十年前,在中国摇滚的中生代,崔健早已这样唱着: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
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花房姑娘》
种花的姑娘亦是花。她的根缠在泥土里,这注定她没有能力“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崔健《假行僧》)”,她吐露着曼陀罗一样迷惘的香气,伸展着常青藤一样牵绊的肢体。这是中国摇滚文本中最早出现,且延续至今的女性形象之一:作为隐喻的植物外阴。无力,虚弱;但充满大地芬芳——原始而单纯的美丽:“你的名字是红叶是香怡是太阳还有月亮/好听的全在你身上(王磊《我来看你了》)”。在最初的通往混沌理想的路上,女性形象坚守古典主义的“乔木->丝萝”定位,指代安定,娇柔,静止,处子般立在蠢蠢欲动的雄性力量对面。
点亮你无力的灯光
我就会觉得暖和
用你的身体搂着我
我不会觉得寂寞
啊 不能 我没有什么给你
我只有送你一朵藏红花 ——张楚《藏红花》
作为消费品的女性之花,同时也作为战利品暧昧地存在。她们被动开放的柔弱姿态是如此惹人爱怜,几乎引发男性最隐秘的施虐欲:
我总在伤你的心,
我总是很残忍
我让你别当真,
因为我不敢相信
你如此美丽,
而且你可爱至极
哎呀灰姑娘,
我的灰姑娘——郑钧《灰姑娘》
可是听,那强者的歌声中也充满了不安:“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象是给我……赞扬/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一样(崔健《花房姑娘》)”,享受着被仰视的快感,同时,也怀着被阴柔同化以及被束缚的隐忧——无比讽刺地暗示男性最隐秘的阉割焦虑。
于是,在面目严厉的警告: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之后,紧随着爱莫能助的悲悯: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
但不是你的泪——崔健《假行僧》
但无疑,这饱含审美情调的凌弱感让男性着迷。与商业化的花儿雷同,二零零零年的朴树仍在唱: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其中不乏温存的牧歌情怀与《花房姑娘》所流露出的毫无二致:“理想”,“流浪”,“天涯”,这些字眼犹如号角,持续呼召着流浪者们脱离温柔乡,走出花房,继续上路,尽管路的尽头很可能只是虚无:“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许巍《两天》)”。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周云蓬《不会说话的爱情》
更甚,这充满情欲狂想的呓语,将花房中的花朵追溯回充斥着情哥哥/情妹妹的乡愁情结:“妹妹叫我一声哥哥/我却不回头/不知是否她已经看见/我满脸的泪水(崔健《浪子归》) ”;只是那漫山遍野的野火花,如同在张艺谋指挥的野合中纷纷倒下的红高粱一样,只是性解放的装饰品,而并非对象。
秋风吹开了妹妹的花裙在萧瑟地飘
青鸟成群地在你的长腿上盘旋
妹妹你可知道我胸口的热血汹涌
象这山谷下的驴儿打滚
妹妹啊把我这快乐的外衣披上吧
那感觉如何?
那感觉如何?
我已经听见了你的歌唱——左小祖咒《爱的劳工》
在貌似淳朴的民谣表皮下面,是包不住的性之利器;“就在我进入的瞬间/我真想死在你怀里(许巍《在别处》)”。“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时/给你一个姑娘(崔健《投机分子》)”,女性几乎成为被物化了的性对象——玫瑰抛洒在人间,热爱艺术的女孩是上帝赐给艺术家的甜品。一应数年后崔健温厚的嘲讽:
她浑身散发着传统的芳香
等待着新鲜的摇滚Rock'n Roll——崔健《新鲜的摇滚Rock'n Roll》
其实,早已有人察觉,那被折断的纤细枝干中流出的并不是植物的汁液,而是人类的体液: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象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
不恐慌么?“每一枝玫瑰都有刺”。不仅如此,有预感说:有一天,它会从玫瑰变成枪炮。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崔健《一块红布》
.童年的委屈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必经之路是:最初的狂热和新奇过后,“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我从来就是另一个过路的人
在感觉中生存
灰色的城市抛弃了我的颜色
使我已习惯了麻醉
在漆黑的夜里
温情充满空虚
在干涸的眼里
布满红色失意
在慌乱的城里
不停的寻找刺激
在苍白的脸上
疲倦尽露无遗——唐朝《选择》
冲出家门才发现,世界残忍,仅持一柄理想之剑是如此轻易便一败涂地。
不是谈论政治 还是有点慌张
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精神压力如今还没得到释放
别看我在微笑 也别觉得我轻松
我回家单独严肃时才会真的感到忧伤
我的心在疼痛 象童年的委屈
这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崔健《时代的晚上》
精神焦虑来得“迅猛而匆忙”,甚至爱情也成了帮凶:“我忘记了克制后那敏感的脾气突然变得更加糟糕了/那是长期的压抑带来的间接反应/表现在爱情的后面(崔健《北京故事》)”。这“童年的委屈”带来的焦渴感带领人们回到记忆深处扒翻,感到疲倦的时候,花房里的迷香便彻底沦为奢侈,所需要的是更强和更有力的免费消耗品。什么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适时地,作为母性符号的年长女性形象出现在摇滚文本中。而自出现的那一刻起,这些“母亲/姐姐”的表征就已经远不止“故乡”,“家”这样简单。
我的家里还有个母亲她时时为我担心,
为了她我还有一点怕死,不敢让她伤心——周云蓬《荡荡悠悠》
典雅而朴素的情感表达无从填充巨大的焦虑黑洞。打着寻根大旗扶摇直上的摇滚斗士们,寻觅的是双乳间的一张大床,那里安全,丰满,柔软,甜蜜多汁,无边的羊水抱慰着他们重返子宫的诉求:“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像个孩子(汪峰《像个孩子》)”。
感到要被欺骗之前 自己总是作不伟大
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
面对我前面的人群 我得穿过而且潇洒 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 挺假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 你想忘掉那污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 说这很美
哦!姐姐!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 我有些困了
哦!姐姐!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 你不用害怕——张楚《姐姐》
在这里,“西出阳关”的戈壁勇士迅速缩水,“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他退回第二性征尚未发育的童年,扬起头,伸出手,呼喊着姐姐:“我想回家”。回家去品尝什么呢?“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父权已被颠覆。而缺席的母亲与姐姐合为一体,“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不再是被仰视的“世上最坚强(崔健《花房姑娘》)”,在“很温柔很爱流泪很美”的姐姐面前,他更缺乏力量,因为需要对方“牵着我的手”,却还安慰着“你不用害怕”;同时,保持着对成人世界的窥视:“你想忘掉那污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这类似自我阉割的虚脱感同时唤起了男性的母乳汲取需求和女性的母性输出需求,是如此动人心弦。
我全部的人生只是一次失去
如果成长只是一次失去
妈妈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这个世界怎么了
那是个错误
那是你犯的唯一的错误——汪峰《错误》
这不仅是吮吸需要,更是对生命本源的诘问。在无奈地走入虚无之前,形而上的终极问题“生活到底值不值得经历”被答非所问为:我的出生是个不由自主的错误,原罪归于母亲。从而永远逃脱了正面回答的责任。
你明白 你是我的母 万分幸福 聚众的手 生命好紧张——张楚《轻取》
则是对命运的惶恐和被动接受。当一切疑问都被归结至作为生殖能力载体的女性身上,“母亲”这个符号已被延拓得“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而自我认同的艰难,在对女性原罪的追讨中最终得到缓解。
可怜多年后的郑钧,还在停电的夜晚撒着娇:
外面的风 风很大 夜晚漫长可怕
我在找你 可你在哪里
妈妈呀 我害怕
妈妈呀 我害怕
别把我一个人留下
别把我一个人留下
我没有权利 我没有权利 选择你
我只有求你 我只有求你 我哀求你
哀求你——郑钧《天黑了》
不仅是肉体,还有精神:
妈妈再给我唱首歌吧
就唱你教给我的童谣
虽然我现在长大了
可那支童谣我忘了——万晓利《妈妈》
什么样的乳房能经得起如此长年累月的吮吸而不干瘪?无怪乎一九九一年发行《姐姐》的张楚在若干年后冷冷地唱道:
这太让人伤神 孩子啊 快松开乳头从怀抱里掉下来——张楚《动物园》
.像是一把刀子
赵小姐姓赵 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
她的名字不猜你就知道 你可以叫她赵莉 赵小莉 赵莉莉
她还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在这里她能吃到东西 还能休息
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可以去对一个男人撒骄
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 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
在一种时候她会真的感到伤心 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
她想她的脸是可以赞美的 她还有够风韵够女人的脾气
她的未来应该有浪漫和诗意 男人会暗中念着自己
在懂手段的男人面前她会沉不住气 她知道这太危险她会吃亏的
最后她的纯洁战胜了好奇 她决定只上街买点儿便宜的东西——张楚《赵小姐》
这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她有个模糊的名字“赵小姐”,赵小姐身上,人间烟火缭绕。通过她,吟游诗人张楚对世俗生活进行了一次温情的言语抚摸。而胡吗个极简旋律的歌谣以木讷隐藏着农民似的狡猾:“唉,明天还是自己找个女朋友吧/光看别人的也不好意思(胡吗个《到四道口换26路》)”,农村草根对城市伸出的第一支细嫩触角也灵敏地落在了女性的身上。至此,摇滚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第一次摆脱脸谱化,开始丰富起来。
我说呀姑娘你别害怕
有谁会总象一朵花呀
上哪找天生的一对呀
我愿为你唱首歌
我愿为你唱首歌
上哪找天生的一对呀——二手玫瑰《采花》
“卑之,无甚高论。”城市底层摔着啤酒瓶,唱着焚琴煮鹤,得过且过的生活哲学。当宏大叙事的泡沫粉碎,迁出花房的女性已经不再“月亮般皎洁光明”,她们走入穷街陋巷来到人们身旁:
打不开天 穿不过地
自由不过不是监狱
你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
谁都不知到底是爱还是赖
钱就是钱 利就是利
你我不过不是奴隶
你只能为了我 我也只能为了你
不过不是一对一对儿虾米
这儿的空间 没什么新鲜
就象我对你的爱情里没什么秘密
我看着你 曾经看不到底
谁知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
就象这儿的空间里
想的都没说 说的也都没做
乐的就是弹吉他为你唱个歌
你别一会儿哭 你也别一会儿笑
我是什么东西你早就知道——崔健《这儿的空间》
不再怒吼,不再咆哮,不再以先锋姿态睥睨人群的前斗士们开始调侃,开始戏虐,开始在幻灭感中玩世。但同时,他们极力保持着边缘姿态:“我一双干净的手和着可以搓出泥来/我就知道那是我已经在街上呆得太久/我可以回去用肥皂把手再洗干净/可我不能去找个姑娘来洗干净头脑(张楚《和大伙去乘凉》)”。虽然“一起乘凉”,“我”和“大伙”仍是分裂的,街上不能呆得太久,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为干净的双手沾染上了庸俗,而“姑娘/不该是肥皂(张楚《和大伙去乘凉》)”。在理想主义四处碰壁后,摇滚精英们以放低身段换来了女性的平起平坐。
你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
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
我打了个哈欠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
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
刚好这时候你还正喜欢幻想
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
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
我说我爱你 你就满足了
你搂着我 我就很安详
你说这城市很脏 我觉得你挺有思想
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 就信了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床单很白
我看见我们的城市 城市很脏
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 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张楚《爱情》
从观赏植物进化到情感动物,从脸谱进化到肉身;女性形象逐渐壮大的每个瞬间,精神力量存在的可能性仍被深深嘲讽着:“你说这城市很脏 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一方面,区别于摇滚文本中传统的情感容器和肿胀摆设:“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崔健《出走》)”,“我知道你失去的远比我曾给你的多/你想要的海誓山盟我没有资格说(郑钧《极乐世界》)”;女性开始从人群中凸显出自身,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
你光溜溜的身子放着光辉
照得你那祖宗三代露出羞愧
你张开了胸怀,你还伸出了手
你说你要的就是我的尖锐——崔健《像是一把刀子》
而另一方面,逐渐丰满起来的女性身体又被强行盖上了货币烙印,承载着知识分子面对商品大潮表露出来的无力和逃避。
你是一个玩具 生活在橱窗里
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买不起
我还能要什么 我还能要什么
都出卖了那么多 我还能要什么——郑钧《陷阱》
走出花房,走入橱窗。光彩照人,贴满条形码,被观看,被标价,被购买,女性形象再次沦入物化的巢臼。这一次,芭比娃娃的造型招来众口一心的声讨: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你说这个故事不是香肠我知道这个夕阳也披不到你的身上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
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何勇《姑娘.漂亮》
爱上了第一位姑娘 我觉得她很不一样
有天我们在床上 你猜她对我怎么讲
没人稀罕你的感情我亲爱的
你最好变得富裕如果你爱我——郑钧《路漫漫》
这一主题在愤怒的歌喉中长盛不衰。相比何勇当年赤裸裸的指责,数年后的万晓利取势更为低下,却在不知不觉中占尽道德先机:
那一天我出门碰见个姑娘
她穿的衣裳真漂亮
我站在一旁偷偷的欣赏
她长得真美 我想
走过来个老头感觉像个流氓
动手就要拽那个姑娘的衣裳
我心里一发热什么也没想
上去就给了那个家伙两巴掌
哎嘿 我表现得很勇敢
哎嘿 那个姑娘得救了
哎嘿 我有一些脸红了
但是我满足了
谁知那个姑娘突然变了模样
一把抓住我那破烂的衣裳
她柳眉倒竖起来眼里露出凶光
说光天化日之下你反了你了
哎嘿 那个姑娘还说你凭什么打我的情郎
这是他给我买的衣裳他动一下又有何妨
哎哟 这可了不得了 哎哟 我闯下祸了
哎哟 那个姑娘急了 他说我是个流氓
到底谁流氓 到底谁流氓
到底谁流氓 到底谁流氓——万晓利《流氓》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玫瑰已然蜕变为枪炮;如流氓调侃家王朔所说:“一把青龙偃月刀”。被人为地武器化的女性形象劈入现实,也许正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新颖的方式,没有更尖锐的力量。而事毕,武者与武器同样鲜血淋漓。
.无能的力量
姑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不清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冷漠的像一块冰
像一块冰
姑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不清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肮脏的像个男人
像个男人——万晓利《姑娘啊,你真傻》
——对女性内心世界探访的背后,是对自我的深深怀疑。在这里,直立起来的女性形象成为观照者的映射和镜像,作为个体的“人”接受疑问,同时也为自我审视提供对象:
你就象是一面能透视的镜子立在我的对面
专照着我 专照着我身上看不见的空虚
这时我感到刚才我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
是因为我只有欲望而没有什么感情——崔健《另一个空间》
作为难能可贵的回答尝试,崔健在《笼中鸟》里唱道:
别说这是美丽 青春的你
你不过是还有个 性感的身体
会有人爱上你 跟你有关系
现在你还太纯洁
现在你的疯狂还是秘密
别说你有爱情 年轻的你
遥远的温情偶像只能在你的梦里
一天你会醒来感到孤独和寂寞
那时你会和我一起
和我一起发现你的秘密——崔健《笼中鸟》
已成经典的女性存在的附属地位被彻底否定。在“美丽/性感/青春/爱情”之外,呼召着对内心力量的关注:“疯狂就象只小鸟就在你心里/一天她会突然跳起/从你的身体里飞出去”。女性,犹如刚刚立起的硬币的另一面,终于在摇滚文本中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第二性产生照应。而随着内心审视的强度逐渐加深,女性形象也逐渐意象化:
给我一个不变的魔术光滑的手
让我醉死在你胸脯赤脚不朽
枯死之柳没有遮荫花开了
秋天的女人半夜点灯焯灼你枕头
你拥有她不孕的子宫光滑的手——左小祖咒《不孕高手》
在这里,失去生殖能力的女性带来多种隐晦意义:性的滥觞,末日恐惧,犬儒主义。
我心爱的女人在山上为人画着
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老鬼
那老鬼年轻的像我可怕的从前
手里握着我为那女人拾的玫瑰
….唉啊
我那女人画着画的快要枯萎
那老鬼为他留下了满山的遗憾呐
听说他在死前一直闻着花的蕊
可是我那可怜的女人没有张开嘴
我努力的攻击着花的蕊
玫瑰呢呢喃喃的说位置不对
我努力的攻击着花的蕊
可我怎么用嘴去唱出这二手玫瑰——二手玫瑰《好花红》
当经典的玫瑰符号再现,那漂亮的花瓣却灰败不堪,散发出下半身和死亡的腐朽气息,笼罩着这一幅肮脏的超现实主义画卷。
她世界最后一颗月亮昏睡在你窗前
赞美吧,被沉默牵引的你和失意的人们
她世界最后一颗月亮仰卧在你窗前
亲吻吧,被誓言捍卫的你和可爱的人们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共产 爱情的唾液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的资产 爱情的裙子
她世界最后的红裙子挂在树枝上
扯下它吧,被沉默剥削的你和失恋的人们
她世界最后的红裙子已被晚霞染褐
戴上它吧,趁你年少还没有花眼之前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共产 爱情的唾液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的资产 爱情的拉链——左小祖咒《羞辱主义》
高度意象化的女性形象与思辩碎片,政治暗喻,世纪末狂想混杂在一起,流露出颠覆一切的绝望心绪。
一个安静的像没有一样的姑娘
坐在我的屋子里
她呼吸如夜晚的草木
她一生只说一句话:
咱们结婚
......
她像没有一样纯粹...
她像没有一样静静的躺在我身边...
她像没有一样给我唱歌...
她像没有一样无声地啜泣...
但有那么一天
她像没有一样地死了——周云蓬《没有》
当被加载的意识形态代码过重,过度诗化,过度抽象的女性形象已与现实疏离到对面不识的地步,那么只好将一切归零——“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沉没在黑暗里了”。同时,在其对面的男性也失去立足之地:“剩下我一个/0/比没有还少”。
请看着我的眼睛 你不要改变方向
不要因为我太激动而要开始感到紧张
把那只手也给我 把它放在那我的心上
感觉一下我的心跳是否是否还有力量
你的小手冰凉 像你的眼睛一样
我感到你的身上也有力量却没有使出的地方
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坚强的姑娘
也许你比我更敏感更有话要讲
你会相信我吗 你会依靠我吗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你无所事事吗 你需要震撼吗
可是我们生活的这辈子有太多的事还不能干呐
行为太缓慢了 意识太落后了
眼前我们能够做的事只是肉体上需要的
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美丽的姑娘
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崔健《时代的晚上》
终于有了肉体,也有了精神;有血有肉的女性走出镜像,走到她的歌唱者身边,“什么都没说/你往下摸了摸/你抓住了我的手(崔健《无能的力量》)”。但当携起手来却只能同看窗外大厦纷纷倾,那枚直立硬币的意义或许仅仅在于一个苍凉的安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是结语的结语
L7,八十年代中期组建于洛杉矶的一支朋克金属女子乐队。她们这首《Lorenza Giada Alessandra》是近年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情歌。“如果这是最后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崔健《最后一枪》)”,现录歌词全本于此,以完此文。
L7 -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Nicola, Alessandra
Lorenza, Nicol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enza, Nicol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Nicol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ahhh!)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Lorenza, Giada, Alessandra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elbourne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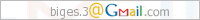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6 条评论:
苏阳《贤良》
你就是那世上的奇女子啊
我就是你身上的拉拉缨,
我说要送你新鲜的花儿
你让我闻到刺骨的香味儿!
关于后面一些主题,我总觉得姑娘爱钱是对的。(谁叫小伙子连钱都不值呢。)
可惜爱钱的时候她们不再吸引人。
所以我的态度是远远地同情。
我总觉得女性个体图景和女性美是两回事。前者具体后者抽象。前者是particular后者是universal。
这里讨论的只是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不是现实中的女性,所以基本上是symbolic或metaphoric。
将爱情和金钱对立起来构成矛盾,然后让女性成为矛盾的现实载体,这种摇滚造句法我个人认为比较幼稚,而且软弱。
完全不能同意“姑娘爱钱是对的”,爱钱或者爱小伙子是个人偏好,谈不上对错。而且两者要一定对立吗?
个人认为,比钱值钱的小伙子多得是。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其实也不全看个人选择,大多数时候天说了算。当然,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要比比二者的级别。
比如 顾城说:
“我什么也没有,你知道,我可以把世界上的东西拿来给你,拿一块蛋糕、一个杓,一个机器,拿一所海滨的房子,放在盘子上,给你。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给你的,谁都能给你这个礼物,你都能接受,你在接受我的时候,就接受了别人,这是生活所规定的。我什么也没有,你知道,除了我的灵魂,除了和这灵魂在一起的不太长的生命。你要它。”
===============
既然他是死囚,他就自己去死好了,为什么要别人接受? 他为什么憎恨别人到“生活里去”? 他为什么用自己的恐惧、孤独、无助来作为要挟、挽留 爱他的女性的筹码?
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和艺人在“生活”中没有自信,寻死做活,谓之“爱情”。
晕了。也不明白哪里说拧了。
“面对姑娘的选择而输给钱(不一定是钱,什么都行)的小伙子...继续盯着这个姑娘,对其进行道德指责”——这“道德指责”正是这些摇滚文本的来源。
文章分析的是文本,结果从中得到作为“道德指责”靶子的女性形象。在这里,只是做为一个事实进行陈述,并没做价值判断。
好像基本是一致的。“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并不在讨论范围。
——忍不住说一句题外话:无论男女人畜,被抛弃/被拒绝后都应该先从自身找原因;不愿挨我操者无耻,这说法虽然解气,但要多傻逼有多傻逼。
6爷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尤其顾城那一段。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自古就惯于躲在文字后面自摸,或者圈个小圈子互摸,或者寻机会找个女人手淫。“交给你的只有灵魂和生命”——这灵魂和生命恐怕也是枯萎腐烂的吧?一同强迫对方接受的还有自己不愿面对的现世负担吧?连最起码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尊重,诚恳,和责任感都没有,谈什么爱情!
其实这种人交个女朋友还不如去养条狗。操,我又不严谨了,等着接动物保护协会的传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