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4日星期三
给옛Товарищейクラス
这几天,有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以及尚未退休的老同志,济济一堂,开了个小会,会议的内容是——网络歌曲恶俗化问题。这些老同志们,尤其是失声很久的老同志,畅所欲言,慷慨激昂,像打雷前的闪光一样,对网络歌曲进行了无情地鞭挞,他们总结出来几句“四字经”:“淫言秽语、宣传色情,辱骂攻击、歪唱恶搞,矫情做作、无病呻吟,东拼西凑、废话连篇,佶屈聱牙、语无伦次,哗众取宠、庸俗无聊。”看来,老同志对网络恶俗歌曲的痛恨已进入木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如果不把网络歌曲斩尽杀绝,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之势。
与会的老同志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想当年俺听流行歌曲那阵子,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徐沛东、傅庚辰、阎肃、谷建芬、李海鹰、付林、印青、王晓岭、曾遂今……俺就是听着这些人的歌曲长大的,实在对不起这些前辈们,俺现在变得越来越恶俗,一边听着《勃兰登堡协奏曲》,一边听着《老鼠爱大米》,我没法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您总得让我有软的时候吧。
反对网络恶俗歌曲,我是同意的,我连网络恶俗留言都屏蔽了,更何况网络恶俗歌曲呢,但不管怎么说,歌曲再恶俗,它也属于艺术表现范畴内的东西。我记得冯梦龙老师说过一句话:“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冯老师说的山歌,就是一种民间创作真情流露的东西,如今,“山歌”被搬到互联网上,歌曲恶俗了,但是相对还是很真实的,它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在真与假、雅与俗的大是大非判断面前,我宁愿去选择真与俗,不选择假与雅。
参加研讨会的老同志当中,有一位老师叫曾遂今。曾老师是个音乐社会学家(权且这么叫),因为他写过好几本音乐社会学的书,我还买过一本,曾老师也加入声讨行列,让我感到很痛心。作为一个学者而不是词曲作者,尤其是研究音乐社会学的专家,应该比其他老同志更知道音乐的社会功用,但是曾老师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我又找出他的书看了看,发现曾老师这么做是正常的,那本音乐社会学的东西真没说出什么观点来。还有徐沛东老师,俺当年可喜欢您的《过三关》这首恶俗歌曲了,每次哼唱,俺都想入非非,打算长大后就这么去泡妞。这首《篱笆·女人和狗仔队》插曲如果今天发行,肯定是最热门的彩铃之一,徐老师可能因为这首歌挣到不少钱。当然,徐老师也许会说,这首歌的歌词是张黎老师写的,自己只管谱曲。还有付林老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无论如何也算恶俗歌曲吧,不仅恶俗,而且恶心。
其实要这这些老同志的“恶迹”,都能找到一些,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去批判一个人,那是文革的做法,揪住人家小辫子不放,我不能因为有人曾经干过错事就剥夺人家说话的权利,这是现在网络傻逼们的思维方式,我真的是支持任何一个脑袋糊涂的老同志发言的,因为这能证明一个时代跟另一个时代没有关系。而我举这些老同志的“恶迹”的例子,还想说明一点是,不管什么东西,它都是相对的,尤其是涉及到社会学和美学方面的时候,都不是绝对的,它的价值也是相对的,对于恶俗网络歌曲,它并非一无是处,至少通过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当今的社会状况。
有一次,我们主编——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主编跟我讨论音乐,他说流行歌曲容量太小。但我认为,流行歌曲可以非常及时反映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心态,这一点是古典音乐做不到的。古典音乐只能体现当初的社会状态,它不能与时俱进(江总对此成语亦有贡献)。为什么人们喜欢研究各个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歌谣呢,这些歌谣大都俗不可耐,但是它反映现实。举个比较久远的例子,有个叫刘邦的花花公子,有一天诗兴大发,脱口而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绝对是一首好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本杂志叫《阅读与欣赏》,作者就这两句破诗写了两万多字的欣赏笔记,看的我头昏脑胀的。这说明这两句话的确有可琢磨的地方,不然就是那个作者闲的蛋疼。几乎是在当时,还有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没有人用两万字分析这句话,因为它缺乏诗意,就是一句牢骚话,或者是蛊惑人心的话。可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面对这句话浓缩的现实中生活,相比而言,它比《大风歌》更有意义。
话扯远了,我们不说古代的事情,说了老同志大概也不明白,以为我强词夺理。这些老同志大概都听过中国各地的民歌吧,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歌都有庸俗、粗俗、恶俗内容,这些歌曲生生不息,流传至今,就是人们都喜欢,占的分量还挺大。而且它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值得人们去研究。但是它从来就没有通过媒介传播,就是因为它是“三俗产品”,我看了不少研究各地民歌研究的书,基本上都把这部分内容省去了,但你不写不能证明它不存在,你到西北去听听“酸曲儿”,到处都是恶俗的内容,“一把搂住细腰腰,好像山羊疼羔羔。花布衫衫扯开怀,白格生生的奶奶露出来。”这种歌词你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吧,但是它快失传了,比什么都宝贵,再不抢救,就没了。你只有到真正的农村,才能听到这些歌曲,什么叫艺术,这才叫呢。所以还是冯梦龙老师看得透彻。多少年来,我们了解真相,就像我们抬头看月亮,总是看不到完整的月亮,有一面总是掩在后面。它客观存在,我们却人为将其遮掩。现在有个了解现实和真相的机会,老同志非要把他捂在被子里。
我想这些老同志大概多少都听过吧,也都“挺”喜欢的吧,为什么在数字时代有人恶俗一下就受不了呢?当然,老同志会说:低俗、庸俗、恶俗。这些老同志推荐的恶俗歌曲我都听过,我觉得最恶心的也没有民歌过分,比如“让你亲个够”“擦掉一切陪你睡”,有什么啊,男欢女爱你都不敢正视,你再正视什么我都不相信是真的。
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内容的东西,它的雅俗都是相对的,关键是你怎么面对它。在1988年,流行了一段囚歌,以迟志强为代表,要说流行歌曲恶俗,那时候最恶俗,正好我赶上了,差不多都听过,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次民声的音乐表达,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摩擦镇痛时期最好的体现,今天我们在去研究那段历史,不要只听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在那里胡说,还要了解一下文化现象,透过文化现象了解历史比那些傻逼专家在家里抄出来的历史还要真实。
还有邓丽君,我最爱拿邓丽君老师举例子,没有她,内地流行音乐要往后晚上五六年,如果这个时间差错过去,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赶不上了,在座的老同志大概都听过邓丽君吧,甚至在家里偷偷都学过邓老师。可是当时邓老师是典型的反面代表,是靡靡之音,不仅庸俗、恶俗、粗俗,甚至还要给她扣上一顶大帽子。可没有邓丽君,哪有后来的内地流行音乐。批判邓丽君的时候,我也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小,我就不明白《采槟榔》《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到底庸俗在哪里?还有那个“流氓歌手”张帝,他现在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要说恶俗,张老师可谓恶俗到了极点,现在又怎样呢?
老同志们,你们都已经风烛残年,流行音乐是永远更新的,你可能写不出今天这种感觉的音乐了,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用恶俗的帽子给某些歌曲下定义,要慎之又慎。退三百六十五万步讲,就算你们批倒批臭,它也不会因为你们的威严而消失。
我想这一点研究音乐社会学的曾老师是最清楚的,恶俗的网络歌曲是当今媒体传播的最好例证。没有传播,谁会去关注它们的恶俗呢?但是为什么传播媒介把恶俗传播出去了,却没有把这些老师们的优雅传播出去?这是个他娘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在1976年以前没有流行音乐,只有革命歌曲,连抒情歌曲都没有。那时候只有革命,你丫没事抒什么情?你的感情你能献给毛主席,你看付林老师就做得不错,人家就写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他那时候打死了都不能写《太阳最红,妈妈最亲》或者《太阳最红,媳妇最亲》。在那个变态的环境中,这些老同志可都是青春期啊,该发情的时候都献给了革命,等到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老同志们的青春期都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的思想也是逐步开放,到了1984年以后,流行歌曲创作才进入到人性化的阶段,不过那时候主题都是很虚的,很少涉及到男欢女爱,更别说恶俗了。1985年我们才写出《让世界充满爱》,爱作为一个主题可以随便写了。可是这时候这批老同志都过了青春期,加上小时候受到的都是革命式教育,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老同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显然是跟不上后来的社会变革,写点中规中矩的歌曲可以,表达情感总有点欠缺。表达上欠缺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欣赏上的欠缺,写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隔着东西就有好多层了。到今天,看到网络歌曲的恶俗,他们当然是无法容忍了。
可是你说谁心里没有俗的一面呢?老同志也是人啊,但是这些受过传统教育的老同志们就像今天意识形态对待粗俗的文化一样,尽可能把用高雅的裹脚布把自己恶俗的一面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变成正义的化身,高举道德的砍刀,向“恶”势力劈去……唉,这样的段子,我们上演了数千年。
还记得有本诗集叫《诗经》吗,风雅颂,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是《风》。但是古代有些老同志就会觉得《风》很恶俗,里面老是男女之情,一点都不主旋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除了生产力发展了,脑袋里那点烂东西一直没有变。我觉得《诗经》分为《风》《雅》《颂》,这种分类太科学了,今天的文化一样是分这三部分,风,就是《悔恨的泪》《纤夫的爱》;雅,就是《今夜无人入眠》;颂,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走进新时代》。几千年我们干的就是一件事。
我确实时听着这些老同志的歌曲长大的,老同志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您不服不行,因为您自身有局限,这又不怨您,因为您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有局限的,看问题自然也不会用开阔的眼光去看。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在认识上都有局限,近视不要紧,但是看问题要有开阔的胸怀,如果还老一套的方式衡量现在的问题,那就是“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人说“四十不惑”,老同志们都五六十岁了,早过了不惑之年,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明白呢?以前我总是教训80后的孩子,你有权利表达,你有资格表达,但是你还没那个能力,所以别什么事都要发言表态,除了证明自己傻逼没有任何好处。而老同志呢,您有权利表达,您有资格表达,但是您的能力在退化。这个退化的直接因素是时代发展太快,把您给甩在后面了,能自身的那点能力系统都不更新升级,在判断上自然会出问题。如果您心明镜一样,只是为了冠冕堂皇说几句违心话来摆摆pose,那您最好shut up,这不跟瞎起哄没啥区别了吗。
我也不喜欢恶俗的歌曲,但我这么看,作为一种类型,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原因来搞清楚它存在的理由,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社会现实。这叫实事求是。我不喜欢我可以不听吧,这是最高的人权,谁都干涉不了我。但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代表老百姓不喜欢,谁授权你做老百姓的代言人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听到老同志来分析这些恶俗歌曲出现、存在、传播的原因,通过分析给我们一个科学判断的依据,但是我没有看到,看到的是一种叫嚣,这是最没本事的表现。
好,您看不惯,憋在心里难受,要直抒胸臆,那就好好讲道理,不讲道理您不就跟现在的傻逼孩子没啥区别了吗。我觉得老同志们至今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不能因为您写过很多流行歌曲就证明您对某些问题就可以发表见解了,创作是一回事,评论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交集,也有您不懂的地方。我认为老同志们最不懂的就是今天的歌曲已不仅仅代表它是一首歌曲,它的内涵您在创作的时候可以把握,外延的东西跟您创作无关。而一个最大的外延就是它要经过商业的检验。这方面,老同志们都没怎么经受过商业洗礼。网络歌曲的恶俗,恰恰证明了一点,它有市场,它的市场就是由一些恶俗的人消费的,你看看乌烟瘴气的网络世界,就知道为什么会有恶俗歌曲了。虚拟的互联网世界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感受,我们祖宗从树上下来之后,一直活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有幸赶上了虚拟世界的开端,但是由于谁都没经历过,连参照都没有,这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这需要我们的后代慢慢来适应和解决。对于恶俗网络歌曲,消灭它很简单,把互联网掐掉即可。可是历史又不是可以逆转的,我们只能面对。您不能面对,就别干让历史倒退的事情。如果您有看不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新您大脑里的破系统,跟上时代,写出真正让人喜爱而不是晚会导演满意的歌曲,去占领网络空间。有好的东西存在,不好的东西空间自然就少了。
有个画家画过这样的一幅画:一群民兵,手里拿着三八大盖,匍匐在一张床的周围,这张床上搭着一个蚊帐,民兵们盯着床,虎视眈眈。这幅画的名字叫《我们一定要占领床》。我觉得这些老同志有点像拿着三八大盖的民兵,想占领床。好,您有这个权利,占领吧,别老整天开会看着别人占领了床而不开心,您真刀真枪来一次,只要您宝刀未老,什么床都能占领。您要是老了,连他妈老婆的床都占领不了!
临渊骂渔,不如退而结网。有本事您自己写出来,跟那些恶俗网络歌曲肉搏PK一下,亮出您的舌苔火空空荡荡,敢吗?今天,我们能听到的流行歌曲已经越来越少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凤毛麟角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时代带来的问题。不幸的是,又让我们赶上了,于是我们感伤了。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一个死去之后重头再来的过程。老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成绩在某种角度看是有目共睹的,今天的事情,你们真看不明白了,就别出来瞎嚷嚷了,保持革命晚节其实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下课!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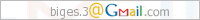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3 条评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刘半农这些北大的名牌教授办了本《歌谣》杂志,第一期上登了三条征稿声明,第一条:我们征集各种民谣,不包括猥亵、淫秽的;第二期变成了“包括... ...”;第三期变成了:“尤欢迎...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稿中发现,最好的、最生动的、最有意思的便是这些带色的。记得一则刘半农整理的民谣,很有趣:“大姐走路俏俏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前摸一把,心儿却是跳跳的。”
虽然我也很少听那些“网歌”,但是文章蛮在理儿的。
杜老汉扯着嗓子唱起来∶
沙梁梁招手沙湾湾来,
死黑门的裤带解不开,
车车推在路畔畔,
把朋友引在沙湾湾。
梁梁上柳梢湾湾上柴,
咱那达达碰见那达达来,
一把搂住细腰腰,
好象老山羊疼羔羔。
脚步抬高把气憋定,
怀揣上馍馍把狗哄定。
白脸脸雀长翅膀,
吃你的口口比肉香。
白布衫衫怀敞开,
白格生生的奶奶露出来。
哎哟哟,我两个手手揣奶奶呀哎嗨哟,
红格当当嘴唇白格生生牙,
亲口口说下些疼人话。
偷情的歌
一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站在奴家门上,
娘问女孩什么响,
东北风刮得门栓栓响。
二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进了奴家绣房,
娘问女孩什么响,
人家的娃娃早上香。
三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上了奴家的炕,
娘问女孩什么响,
垛骨石狸猫撞米汤。
四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脱下奴家的衣裳,
娘问女孩什么响,
脚把把碰得尿盆子响
由此还有一首无人不知的《东方红》,在其原来的民歌基础上改变的《白马调》:
白马调-东方红的原歌词
(东方红的曲子就由它而来,这是没经革命化处理的原歌词)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
呼儿嗨哟
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哟
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
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
《骑白马》已经是改编过的版本。这个曲子的元版是《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
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也正因此,后面几个版本中都会有“三哥哥”这个形象。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