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
等待·永恒
雨开始下的时候,我刚刚醒。我躺在床上,看见对面墙上的钟,九点十分。我盯着它看了很久,觉得它一动不动,后来我不看了,任由它留在那时刻。
我不用转头看,也不用伸手摸,就知道朱萸已经离开。我独自躺在床中央,好像床的皇帝一样。阴茎在被子下面垂头思考,我回旋着飘向天花板,却被它坠住,我就用这个怪异的姿势闭上眼。
“她的身体变得陌生了,他很生气,把她从床上揭起来扔了出去。她哭,他让她滚,他知道她心里另有别物。她就走了。他挑了一把很锋利的刀,藏在怀里,每天在静僻的街道上乱走,他想,只要遇见她跟别人在一起,就砍死他们。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夜里,他终于看见了她和一个人走过来,月光照在那人的脸上,他丢下刀跑了。他发现那个人是多年前的十八岁的他自己,他就是他,她为他背叛了他。他怎么能杀死他呢?一旦这样做了,他便会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
—— 朱萸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电脑键盘上敲如上文字。她走进来我就不写了,把椅子转过来看她。朱萸站在房门口,环视一圈,然后走到床边坐下,小心地把自己的两条腿并排放好。她这一圈环视让我凭空觉得我的房间缩小了五平米。现在朱萸离我很近,我再看看她,发现她有点紧张但心情不错,一副马上能打开包瓜子开始磕的样子。她把手里的钥匙递过来说,还你的钥匙,收好了。
我伸手接过,说,你混得不错吧。朱萸笑笑,不动。
瓜子皮一片一片落在我的地板上,上面还沾着令人恶心的口水。一个女人翘着二郎腿磕瓜子的形象使我怒火中烧。
我又说,别跟他混了,人家已经结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朱萸还是笑笑,不动,松了一点。
我把钥匙扔到桌上,当啷一声清脆无比。朱萸看我一眼,从书桌上拿起我的水杯喝水,双手握着杯子。朱萸的手在我眼前发光,那是她全身精华所在,细滑白皙,不动的时候像玉人入睡,动起来像玉人起舞,摇曳多姿。我盯着它们,觉得阴茎被轻轻握住,正在优雅地上下套弄。没过一会儿我烫了,我站起来夺过朱萸手中的杯子扔了出去,它砸中了玻璃茶几,把圆润的转角砸出一个匕首,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把杯子扔了将朱萸拉进怀里,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收拾好了她,摆在床上,朱萸既不配合,也不挣扎。我半跪在床上看看朱萸,再看看,束一下身心,掏出阴茎对准她,她望着窗外根本不与之对视,好像那里有根电线拴着她。我掂掂手里的家伙,很沉很硬朗,我俯下身去用手板正朱萸的脸,我的目光直插进她的眼睛,然后阴茎也慢慢地插进去。朱萸忍不住抽搐一下,从鼻腔叹出一口气。我感到了温热柔软,然后我提起来,我凉了,于是我又插回去。朱萸好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黄油在慢慢融化。我是一把滚烫的刀不断向敌人刺杀,朱萸终于忍耐不住放出了呻吟,她张开四肢把我网在里面勒向她。我的上半身一个俯冲软在她身上,而下半身如加满了煤的机车车头一样响着汽笛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拉不住轨道,我腾地烧大了,昏黑的房间被火焰吓呆了,我和朱萸的影子映在墙上也把墙吓呆了,它们都不敢出声。朱萸半合上眼皮,红了脸颊,嘴唇亮闪闪地湿着,头发撒得哪里都是。我感到她的最深处在微微颤抖,于是再使劲插到更深的地方然后毫不留情地拔出来,朱萸蛇般扭动着,发出嘶嘶的声音,她的身体已经化得洇在床单上,只待最后一刀。我忽然停住,我看见朱萸在枕上轻轻别过头去躲避我的呼吸。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和朱萸已经永久地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
现在雨下着。我记起来,后来我躺着,朱萸从我的枕头下掏出一个烟盒,打开看看,问我是什么。我说这是大麻,你要不要尝尝我可以教你。朱萸裹着被子坐起来说要,全然不顾这一动作使我光着屁股大白于天下。我下床摸到书桌抽屉里的烟斗和打火机装备好,光着屁股给朱萸示范怎样点火,怎样闭气,怎样让好东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更久。后来房间里有了雾,我看不清我们是怎样分着抽完小半盒大麻的,朱萸后来又怎样从地板上拾起她的衣服穿戴好,系上鞋带,开门出去。她到底回没回头,我也没看清。我睡着了。
雨还在下。我把自己拉起来,找到短裤上衣套好。我坐在床边,想喝啤酒,就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得步履蹒跚,我的腿磕在玻璃茶几的角上,轻快地蹭了一下。我想,飞得有点高。这时雨好像已经下到房间里来了,我身上开始湿了,我要去屋外躲雨,就带上门出去。谁知屋外的雨并不比屋里小,连楼道里也湿漉漉的,我伸手摸向楼道灯开关,但是开关不在那里。我只好在黑暗里摸索下十二楼。半夜下楼买啤酒的时候我从来不坐电梯,深夜里的电梯让我有幽闭恐惧。
卖啤酒的小卖部离我住的楼三百多米,我站在楼门口看见模模糊糊一团光,知道还没有关门。我不知道卖酒的老板叫什么名字,虽然我已经从他手里买了三年啤酒。那人生就一副龟头感很强的模样。每次他从窗口深处伸出头来问我要几瓶酒,我总感觉自己是在与一根狡黠的,带眼镜的大鸡巴对话。此人持续地令我忐忑,每当他把啤酒递给我,我都下意识地缩一下头,躲过他扫过来的眼神。我的直觉是,他是一个专门为我埋伏下的阴谋。此时,我觉得他正在屋里点着灯,他知道我今晚必将到来,他脸上涂着一层莫测的笑容,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啦。我这样一想,全心害怕起来,腿就软了,我找到路边坐下,等心脏慢慢安宁。雨很暖,与我的身体没有温差,雨泡着我就像瓷罐子里的醋泡着白菜。
不知道朱萸是不是已经到家了,真希望她飞在半空看看雨,如果她不怕高的话。
朱萸裹着被子坐在我床上,漂亮的手端着烟斗,深深吸着里面的气体,气体灰色带毒,吸下去她就脏了,就算把她从里到外翻过来刷一遍也洗不干净。她很快地腐朽,连皮带肉一起烂掉,最后她惨白的骨头摊在床上扭来扭去,嘶嘶吐气,等我给它最后一刀。这一刀真是困难啊,失去摩擦感包裹的阴茎根本无法确定方向,它看着眼前庞大的骨盆,觉得举目无亲。
现在我不知道雨是不是还在下。我听见水静静流淌的声音。小卖部的老板打着一把伞,俯身对着我,伞遮住了他的脸。许多水从他的伞上滴下来,滴到我的腿上,汩汩地流到土地里不见了。我伸手过去把伞移开,脖子以上,他的头应该在的地方,一个硕大的龟头正看着我。
我在重重的颤抖中惊醒。摸摸我腿上,梦里伞上的水滴过的地方,那里有个不大但很深的伤口,外翻的皮肉已经被水泡得发皱,有很多水流出来,也有很多水流进去。明天早上起来我会坐在这里,身体里装满了水,丰盈清澈得像一个可以投进硬币的池塘。
我是陈牧,今年三十四岁,死于大量失血,原因是雨水阻止了血液凝固,大麻又麻痹了痛感,使被玻璃割伤的创口未被及时发现。总之我死了。
我算是个极健康的人,除了略微酗酒、轻度神经过敏和偶尔吸食大麻之外,我很正常。我靠为画家朋友们写画评,为小说家朋友们画插图为生,收入经常稳定,认识的姑娘很多。朱萸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有点记不清认识朱萸之前,我身上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情,只是肯定有。我死了,又还在飞,记忆像酒精一样挥发是个必经过程。我在减负,非常舒服。但我还能依稀记起我见到朱萸的第一日,那天刮大风,大风吹鼓了天上一个飞舞的白色塑料袋,使它变成了月亮。朱萸从月亮里一步走到阳光下,她那迟迟熬不过去的恶梦一样的青春晃得我睁不开眼。我就决定爱上她。
不过我只做到了跟她睡在一起。
作为一个死人,我想说爱情就像造小人一样,一个人是干不来的,两个人也未必干得好。我,还有朱萸,曾经一起造了一个很小的小人,它一开始是白色半透明的,很胆小,不敢出门。后来忽然有一天它长大了,变成了不锈钢那种颜色,它推开门就跑走了,我在背后叫它,它根本不理我。当时我觉得,一个白眼狼。
现在我死了,死得死死的。我不再关心这些。我也不关心朱萸会不会知道我死了。永恒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每隔一千年飞来一只鸟,衔走一粒沙子。永恒就是这种等待。我坐在这里死着,朱萸走得再远,也没有我离她远。我可以自由地飞。但是一想到从此以后所有的飞行都再也与朱萸无关,我还是不禁有些遗憾。因为此时此刻,在我看来,朱萸的一生将比永恒还要漫长。
04/04/2008 Beijing
出处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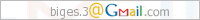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