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
叶三:死约
昨夜陈牧又梦到了那个姑娘。她站在道路的另一边向陈牧伸出手臂,眼神温柔。早晨醒来,陈牧盯着天花板对自己说:这是命该如此。
陈牧出生在一个中型省会城市,他是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陈牧母亲怀孕那年,陈牧的奶奶心肌梗塞死了。陈牧的母亲死于难产。陈牧三岁那年父亲死于晚期肝硬化。从那以后陈牧跟随爷爷生活;直至十六岁那年,他最后一个亲人死于直肠癌。
陈牧的爷爷生前是个高明的修表师傅。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花了十年把自己所会的一切都教给了自己的孙子,然后花了三个月在医院里痛苦死去。爷爷死去之后,陈牧渐渐发觉人们看自己的眼光开始变得奇怪。“这个孩子身上有死气。”很多人这样说。陈牧对此感觉混沌,毕竟他当时只有十六岁。
两年后,也就是陈牧中学毕业那一年,他最亲近的,也是唯一的好朋友罗宋在他们就读的高中跳楼自杀。据说,自杀的起因是二两猪肉。事情久远,陈牧渐渐回想不起来从二两猪肉到从十二楼跳下来之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总之很恐怖。事发以后,陈牧生活的那个城市为之肃穆一周。在流言纷起,人心杂乱之前,陈牧收拾行装离开了那里,来到甲镇并生活至今。
走在离开家乡的路上,陈牧想,他是死神砧板上的一条鱼,死神正在把他身上的刺一一挑掉,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成年人,他不该再给别人添麻烦。
甲镇是个比麻雀大不了多少的小镇,它的建筑地图和人际关系网都已经千锤百炼,几乎水泼不进。作为一个外乡人,陈牧在甲镇的生活却相当顺利。对于他,甲镇人的木讷恰好中和了好奇,陈牧当上了一个修表师傅。既然甲镇从来没有修表师傅,那么陈牧的出现就顺理成章。刚到甲镇的日子,陈牧几乎可以说是快乐的,他从小就迷恋于与精密仪器的智力搏斗,当一块表在他手中滴滴嗒嗒地走动起来的时候,陈牧觉得自己就是时间之王。甲镇的陌生也让他感觉安全。傍晚时分从修表铺走回家的路上,陈牧有了闲暇看一看周遭的季节,和遇见的那些没有名字的脸孔。他甚至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养了一盆花。
可惜好景不长。
来到甲镇的第二年春天,陈牧的房东——一个爱养猫的老太太——送给陈牧一只刚刚断奶的小猫。陈牧明白,房东老太要么是出于好心,要么是闲得突发奇想。他安慰自己,也许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可是接过小猫的时候,陈牧哆哆嗦嗦。在他的手里,那只不过几个月大的猫抬起头,陈牧清楚地记得,两只惊恐的猫眼一眨不眨地定在他脸上,过了几秒,猫挣脱他的掌握钻到某个角落里不见了。当夜,陈牧失眠,他试图在黑暗里感知在他的房间里是不是有一只猫,或者另一条命的存在。他竖起耳朵听,甲镇的夜晚非常干净。他睁开眼,再闭上,再睁开,他看见两只惊恐的猫眼的特写。他非常想下床去,打开灯,做地毯式搜索,可是从床到屋角开关这五米路,陈牧迈不出第一步,他觉得只要他的脚一踏出去,他就完了,有些可怕的事情就会无可挽回。
后来陈牧再没能找到那只猫。两个月后,房东老太死于肾衰竭。
自那以后,陈牧把屋子里的盆花丢掉了。他还把修表铺的窗户封死,只留下一个可容一只手进出的小洞。他不再与任何人主动讲话。陈牧周身挂着两个无形的字:戒严。有一天,陈牧无意间站在了镜子面前,他猝不及防地抬起头,有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一双猫眼。
陈牧何时开始做这个梦的,他自己也记不清。虽然是个修表师傅,陈牧自己却不带手表,他的屋子里也没有挂钟或日历。反正他第一次梦到那个姑娘,总是丢猫之后很久很久的事情。那个姑娘站在道路的另一边向陈牧伸出手臂,眼神温柔。在梦里陈牧很清楚自己是在梦里,从第一次开始,陈牧就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想要朝她走去,然而他用尽全身力气却还是无法动弹。每每在大汗淋漓中,陈牧愤怒地又无奈地醒来。他发现自己做梦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早些时候,梦后,陈牧会冷笑着想,这又是新把戏。他对自己说,那姑娘就是死神,而他,当然是死神最喜欢的玩具。我不参与这游戏,陈牧告诉自己,我玩腻了。后来他却越来越怀疑,在梦里,虽然他寸步不能移,那姑娘却越来越靠近,有几次,陈牧闻到了她的头发的湿湿的味道,和她的身体的暖烘烘的味道,还有她的手的白白的味道。如果你是死神,陈牧绝望又向往地在梦里想,你干嘛不直接把我拿去呢。几次过后,睡眠就变成了折磨。每天陈牧上刑一般地去上床,他盼梦到她,又怕梦到她,他睁大双眼苦熬天明,结果不知不觉睡着了,睡着的结果,有时候是一夜无事,醒来怅然若失;有时候又是一夜挣扎,醒来精疲力竭。哪一种都不像是长久之计,陈牧想。于是陈牧又想,什么又算长久?
有一夜,陈牧在挣扎中似乎向前移动了一小步。巨大的狂喜席卷着他,他看到姑娘的指尖离他只有一点点距离,他拼命地将身体向前倾,就在他接触到她的那一瞬间,梦醒了。
陈牧看见自己的阴茎高傲地昂着头,将奶状的精液喷得漫天遍野。
那天,陈牧在修理一块古董表时,意外折断了一根纤细的秒针。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中的镊子和放大镜。在秒针折断的时候,陈牧的心底如春河冰裂,多日来的焦虑统统化为悲哀。她也许真实存在。陈牧想。她就在某处等我发现她,然后爱她。梦是她强烈的爱意。——当然事情很可能不是这样,但如果事情是这样呢?陈牧把脸藏在手心里,品尝着唾液甘美的味道。我这样梦到她,想她,她会不会死?陈牧问自己。爱是没有问题的,死固然也没有什么。可是,人们围着姑娘的尸体痛哭流涕的场景让陈牧心生沮丧。不,事情不能这样。
陈牧就回家去了。他最后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如果我连续十天梦到那个姑娘,那么在第十天上我就结束这一切。
昨夜,正是第十夜。连续第十次陈牧又梦到了那个姑娘。她站在道路的另一边向陈牧伸出手臂,眼神温柔。早晨醒来,陈牧盯着天花板对自己说:这是命该如此。说过了,他就很振奋。他跳下床,拉开窗帘,撒尿,淋浴,找出干净的衣服穿上,然后又煮了个鸡蛋吃了。做完这些,陈牧走到桌边坐下,掏出纸笔,想了想,写下两个字,“遗书”。
“与人无尤。”另起一行,他写。然后又想想,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了,陈牧心里十分安宁。现在做什么呢?陈牧再想想,随后把纸翻过面来,依次写下:跳楼。卧轨。剖腹。服毒。割腕。上吊。投水。
首先,排除卧轨和投水。离甲镇最近的河流,走路要四个小时;离甲镇最近的火车站,走路则要五个小时。陈牧认为,完全不必在这件事上花费这么多时间。
排除跳楼。陈牧记得罗宋从十二楼跳下来之后的样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猪血的破口袋被用力掼在了地上。他远远地看一眼就足够了。何况,甲镇根本没有六层以上的建筑。镇政府的四层小楼虽然地处幽静,但楼脚下却有个碍事的自行车棚。
排除剖腹。不可能找到长达一尺的利刃。
在剩下的三项之间,陈牧犹豫了许久。服毒的好处是容易操作,陈牧知道,安眠药只需要四百片以上,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目前市面上药物的质量无法保证,陈牧希望有把握。至于割腕,很适合精于手工的陈牧,他想,在肌肉和腱鞘组织下,找到动脉并割断应该不太难,问题怎样使血液不凝固。照理说一个浴缸是必要的,但陈牧没有。他想将手臂浸在脸盆里难免有些寒酸,而且在大量失血导致神智不清后,手臂的位置也许会移动,以至于前功尽弃。陈牧将两项全部排除。
上吊。确实,简单,高效。一个合适的角度,百分之二的压在颈部的体重和十分钟,任务完成。陈牧想,如果我是时间之王,那么上吊就是自杀之王。唯一的瑕疵是,事成之前,陈牧不免会勃起射精。想起他的精液会从裤管里滴滴答答直到地上,吸引来成群的红蚂蚁,陈牧有些黯然神伤。不过,决定的事情就是决定了。陈牧将纸折好,收到上衣兜里。甲镇有的是健壮的树木,他需要的只是一根结实的绳子。
在屋里转了三圈,陈牧发现,他竟然没有腰带,灯绳,或者电线。他茫然若失地在床上坐下。一些琐碎的市声从半开的窗子探进来,陈牧抬起头看一看,他决定出去买一条绳子。
陈牧出了屋门就沿着大路向前走,看到一间房子,他敲门进去说“我要买一条绳子”,人们看着他,摇摇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走了出去,继续沿着大路向前走。很快他又看到一间房子,于是他又敲门进去,说:“我要买一条绳子”,人们再次看着他摇头。走出了很远,陈牧进了又出很多的房子,却还没能搞到一条绳子。他不禁惶恐起来,他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又把这个游戏玩错了吗?——慢着,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游戏吗?陈牧越想越害怕,他觉得自己自从出生就被一个满怀恶意的游戏逮住了,他怎么逃,其实都在规则之内。于是,他也顾不得找绳子了,他迈开步子跑了起来。
现在甲镇已经离陈牧很远了。陈牧的步子沉沉地砸在大路上,路边不再有房子,而是黑乎乎的山一样的东西。对,天黑了。陈牧一边跑,一边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啊?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静静地洒向他的身后。路上开始出现大型的运货卡车,怪兽一样从陈牧身边掠过去。陈牧非常累,但是他停不下来,他的每条腿各一千斤,上半身却轻得像漂浮在空中。他机械地运着自己的身体向前,他听见半空中有声音在对他说:加油!加油!
最后,陈牧在路边坐了下来,他把头埋在两腿之间。他实在太累了,他想,让我睡一会儿,再继续跑吧。他忘了有梦这一回事。路上的大卡车飞驰来往,就像水里穿梭的鱼。他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道路的另一边向他伸出手臂,眼神温柔;陈牧就走了过去,他看到那个姑娘也在慢慢地向他靠近,他伸出手去,他就握住了她的手。陈牧想:我幸福死了,我一定是死了。
参考文献:《完全自杀手册》(《完全自杀マニュアル》),鹤见济(Wataru Tsurumi),04/07/1993
出处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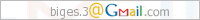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