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30日星期五
瓦西里的意象--逐渐的失去规矩
一个叫“MAO”的地方。MAO被光芒穿过,上边的伟人发际线被光芒穿过。“A”字的塔基中间有一个“.”,是痦子。灯光开始一下一下闪烁,忽然黑暗忽然光明,雷电到达心间。三个年轻人提着武器,忽然走进自己的音乐之河。我听到巨大的铁锤在敲打钢板,像是被抛弃在一个即将倒闭的国营工厂,那些工人流着汗,要敲碎整个地球。人开始来了一些。有一个像是矮小的日本游客,听到猛然的声响,不禁点头,不禁咬紧腮帮,不禁屈臂捏着拳头,不禁匆忙去拍照……有一个是修女,像雕塑被河流穿过,像脸庞被河流穿过……有一个外国中产女子,忽然记得自己是在中国,抛弃了妇德的禁忌,又被妇德提醒,只是任斑马裙子微微颤抖,像是得了轻微的癫痫,像是树被风吹过……有一个男子穿着经理的服装,带来一个涂抹了紫色口红的女子,两个人冷静地喝着矿泉水,警惕地看着另外一个世界,满脑子都是妓女和鸭,要是那样就好了,现在就是那样……有一个平头的男子戴着窦唯式的眼镜,坐在地上,和他坐在一起的是温柔的女子,两个人好似吃了摇头丸,把头颅按照V字的轨道摆过来摆过去,摆过来摆过去,没有尽头的永恒……有一个外国少女总是大幅度地屈膝,肥沃的牛仔裤下边藏了很多的垃圾食品,和一条内裤的边线……有几个外国男子,文静的不文静的,忽然找到了在中国过夜的方式,那就是呈现西方人民在自由方面的优越感,他们像舞着叉子一样舞着双手,他们叉干稻草来了,他们后来又跳起来,像是装了弹簧,就快要撞到天花板了……他们这么血液澎湃,是因为中间有个褐发女子大幅度地舞了起来。这个女子像是一条肥瘦适中的蛇,像是慢性触电,那些头发前后左右地摇起来,那双手溺水了,那腿一抖一抖,那臀部呼之欲出,那裙也太短了,以至于她不时要过去扯下裙摆。她发出了母猿式的尖叫声,啊,啊,啊啊啊……两个中国孩子受到鼓励,以互相打架的名义绕了过去,好好看了几眼这老大帝国过来的尤物……啊,啊,啊啊啊。
你不知道是被统治了,还是被侮辱了。你不知道自己是空掉的啤酒瓶,还是盛大烟火的尖头。汗水汹涌汩出,钢铁被砸的响声越来越响,像是末日的钟声,像是时间停止前的蹄声,像是精子在半空停滞,不再落下。
这个时候,你唱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是唯一的合理。你占有夜晚,庄稼,和上帝,剩下的是傻逼和未来。
未来未来,未来有三个穿破牛仔裤的老男人,带着失聪的耳朵,和彼此勾心斗角的记忆,坐在各自的角落,一下一下地喝着。
垃圾的气息升起来了,泥水的气息升起来了,地震早过去了。艺术像注入阳具的血,干涸了。阳痿了,灰白了,包皮长如猪肠,污垢遍地。
停止,停下钟声。
一个不知名的旅馆,塞在淤积的昏暗水泥中。我来到这里时,整个城市像是刚被洪水洗过。可是每个人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习惯性,他们重新涌入酒馆、被窝和自杀的楼顶。没有什么不是他们熟悉的,没有什么不是他们掌握的。只有我,忽然丢失了铠甲,毫无安全感地站在暮色里。我没有办法逃避自己,我再也寻找不到隐藏在水泥和街道的秘密。在另外一座城市,在我拥有一张床的地方,我把自己的气息留在被窝和窗台,在交通规则之外选择了一条隐秘的路。我和那个我熟悉的城市拥有着太多愉悦的阴谋,我会扶着天桥的栏杆缓缓走下去,会像母亲看着孩子一样,看着环线上奔驰的车辆。可是在这里,我被陌生的雨掩杀了,我寒冷孤单,看够了自己的手、脚和无意义的鞋袜。我必须规劝自己去忍受一首错误的歌,和一些错误的电视节目——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的也是这些。我像是天上的人忽然掉落在一堆泡沫中,我看到一动不动的空气和紧闭的窗户。窗户之外,是灰暗而遥远的街道,遥远而无止境,像是可怖的未来。我被陌生镇压了,瑟瑟发抖,好似眼泪汪汪,却是什么也没涌出来。
我被迫与我共处。
我丧气地躺在床上,开始想到一个我灵魂出窍,他带着惶恐的兴奋,联系上一个嘴角长胡子的侏儒,他什么也没说,侏儒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进了一辆面包车,随着内心的目标驶过一排又一排水泥房,一座又一座加油站,他们来到郊外的旅馆。他听到侏儒和老板耳语了几句,老板笑了,把他送到一个臭虫遍地的房间。他躺在肮脏的床上,像一根性欲极强的冰棍躺进木箱的破棉细里。他脱掉裤子,然后进来一个提着小包的年轻女子,她和他一样只是脱了裤子。她是经济实用,他是矜持,这样关系便被带入到一种纯粹的交易中。女子的雀斑一动不动,忽然说出话时,方言像喷薄而出的大蒜味。他有些像是盲人,被慢慢导入到一个乱石缝中。他像是沙袋,接受拳击手套的夹击,然后听到一句,好了,我走了。
MAO,MAO,MAO下边有个痦子。
我从幻想中归来。好像觉得这是一次不值得尝试的尝试。好像我站在路口时,终点的废墟就已一览无余。然后我极其失败地躺在床上,数着天花板上的损伤,那些奇形怪状的构造很快就失去了意义,那些凹陷掸开我的目光,说:走开走开。我便重新悲哀地躺到深处,躺着而处处看见自己。然后我开始相信奇迹,我把被子和床单掀开,发现了很多细小的龌龊。我继续翻,我相信很久以前一定也有这样一个抓狂的人,他在这间他乡的旅社不能自处,不能忍受,他在拿拳头撞击墙壁和玻璃,他把方便面的遗迹洒了满地,他对着死硬的城市大喊大叫,他最后把疲倦的手放在疲软的阳具上,一次次摩挲顺滑的阴毛。然后等待井口喷出点石油来,原以为那是刺向天空的利剑,却只是有些咸平的东西呕了出来。高潮在还没到时就结束了,他像死了一样捉着自己肮脏的下身。他被时间杀了。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人,住进了这间陌生的旅社。
我继续翻,我把席梦思靠到墙上,床板上只有一只臭虫的尸体,像是被拳头击杀过,如今像脱落的油漆,盖在平面上,一吹就飞走了。我想那个寂寞的人一定不会失约,他一定把东西收藏到了最后。我钻到床底的黑暗中,四处摸,摸出一双已经失去臭味的袜子和几只塑料袋,然后又摸到床脚里头一本耷拉着身体的16开杂志。
我欣喜地把它捉了出来,抖它的灰尘,却发现怎么也拍不完。后来我知道,这些是书本身的土黄色。我去洗了个澡,去刷了个牙,回来后,蘸着口水把那本法制文学读到了天亮。
宽慰我。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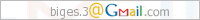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