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本·拉登, 你在哪儿
2004年,摩根·斯伯罗克在拍完记录片《大号的我》后体重增长了近20斤,还收获了高胆固醇、高血压和一只坏肝。这个电影演的是他一个月内不吃别的,只吃麦当劳的生活,后来片子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赞誉,被奥斯卡提名,叫麦当劳害怕(取消了美国的超级大号汉堡包)。事后他花了两个星期来治疗那被肥油占据的肝,花了14个月来减肥,期间反复反弹,他的妈妈欣慰地说:“这下你总算理解了女人。”现在摩根·斯伯罗克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可是他的精神没有。他意识到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一个又一个坏点子在他脑袋里嗡声作响,他成了一全职记录片导演,专门用夸张荒谬的表演和全然客观的记录形式来嘲讽权势,赢取了“电影圈的奸细”和“坏点子大王”的外号。他最新的坏点子是寻找本·拉登。
记录片《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的海报模仿了印第安那·琼斯系列,摩根·斯伯罗克骑了头狰狞的骆驼,穿越炸弹纷飞的沙漠,下有一行大字: “发现之旅”。也许可以被当成个风光片,电影囊括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风景,但在或者辽阔或者破败的风景中央,总有那么个小人儿,他孜孜不倦地仰天发问:“本·拉登,你在哪儿?”那正是摩根·斯伯罗克,他向每一个邂逅的人问起这个问题。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说: “是本·拉登宣布了美国人在中东的合法。”一个以色列记者说:“我们双方都是他的人质。”一个阿富汗人说:“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把他撕成两半。”旁边一老头问:“本·拉登谁呀?”摩根·斯伯罗克答:“他炸毁了美国的大楼。”老头很愤怒:“干他!”过了一会儿老头又加了一句:“干美国!”
这是部制作精良、装模做样、假英雄气十足的电影,摩根·斯伯罗克在里面化名“花花公子”(Dude),他完全假装自己是一傻子。这个花招在拍摄《大号的我》时使他不会被当成个比麦当劳还糟糕的哗众取宠者,到了《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他用地缘政治学、恐怖袭击和战争来炮制汉堡,他不是个愤青,反而自我塑造成个政治观点暧昧不清的土包子。在阿富汗,他跟美军混了一阵儿,被允许扔一颗手榴弹,笨手笨脚后他叹:“糟透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他把脑袋钻进一处洞穴,大喊:“呀——呼——,奥萨马”,没有任何回声。当他身着防弹衣头顶滑稽的探测器抵达瓦奇里斯坦(巴基斯坦西部),那个半自治的部落地区是许多专家高度怀疑的拉登藏身地,边界上立一小牌:“外国人禁止入内”,摩根·斯伯罗克对着镜头说:“确实该有人抓住他,但,那不是我。”他掉头回走。电影以老歌《为什么我们不能成朋友?》作为结束。
《大号的我》之后,摩根被称为“小号迈克·摩尔”,对此他深感荣幸。这位前二流喜剧演员,长期的无家可归者,被电影学院踢出去5回的倒霉鬼,仅仅玩了一把票就成了名导演,这叫他受宠若惊,他保持着恭顺谦良,并不擅长唇枪舌剑,或者说,除了拍摄的都是记录片,他与迈克·摩尔几乎没什么相像。小号的摩根 ·斯伯罗克并不急于把自己塑造成个左倾工人阶级代表,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事嫉俗,他不流露极端的政治观点,不要眼花缭乱的选择性包装,反而充满了个人趣味和游戏精神。
《大号的我》的创意来自一条新闻,有天他缩沙发上吃薯条看电视,说有两个女孩正在起诉麦当劳使她们发胖,摩根心想:我一闻见超大号汉堡的味儿嘴巴就像只汩汩冒口水的狼狗,却总也吃不胖,何不一试。拍摄《大号的我》时他不发表任何观点,只是一天三餐准时出现在大M标志下,片子公映后他只在采访时说过: “麦氏薯条完全不像食品,倒像是人造的、黄色的、长条的塑料制品。不过,吃不吃由你。”最让他兴奋的不是被奥斯卡提名,而是路上遇到有人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快餐。”而不是有人大骂:“我恨你,你剥夺了我的孩子吃麦当劳的乐趣。”
之后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电视节目《30天》,把《大号的我》所创立的“真人秀记录片”形式拓展到新领域:30天内,尝试当一个穆斯林,一个酒鬼,一个被扔进GAY圈儿的直男……摩根·斯伯罗克亲身出演了一集,他和他老婆搬进棚户区,干着只拿最低工资的活儿,每天累得半死,却依然不知道下顿饭吃什么。他们体会了30天低保户生活。“真是段怪经历,当一个穷人每天一睁眼就有人管你要钱。可如果银行里有了一大笔钱,突然什么都免费了,什么都变得又便宜又便捷。”他还照着这个路数制作了记录片《第三波》,在印尼海啸结束后,带了4个志愿者抵挡当地村落帕拉利亚,去记录和体会那里的心碎与重生。
寻找本·拉登大约是他最接近政治的一次,这个坏点子却来自他的老婆宣布怀孕的消息。“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不再使用尿布的时候,美国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恐怖分子?”他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回答。电影同步发行的还有一张游戏卡,上面是很Q的卡通造型基地组织首脑和一只大坦克,以及一套本·拉登小人跳舞游戏盘,正经不错的满月礼物。最终,他当然没有找到拉登,却找到了更多答案:他仿佛体会到那个人之所以成为本·拉登的原因;他感受到中东人狡猾的分裂,他们仇恨美国,却喜爱大手大脚又傻忽忽的美国人;他甚至梦想着能为更深入的对话打开一扇门。至于给孩子的答案,希望有一天他/她看到了电影,说,我想出去转转,去看看世界。
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答案是,可能吧。1934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露出浓密的胸毛。他没有穿内衣。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这个逸闻无从考证,却是好莱坞最津津乐道的段子,它所营造的假象和企图把电影当成一门社会工程学的幻想,在这二年得到更多回应,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还可以改变战争,饥饿,全球变暖,垃圾邮件,血钻。可一看到这种说教式大片,我就想起费里尼的《小丑》和他对小丑的阐释:“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即使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成收获,把空虚变成期待。”摩根·斯伯罗克还不至于被称为大师,但他糟践自己的手段和暧昧的观点,那种不去体会歌星、名模、企业大亨的生活,反倒认真感受穷困、恐惧与混乱的真人秀表演,也许更会叫这世界为之改变。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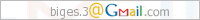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