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癜风”之名,这位非洲后裔将最后一丝黑色驱赶到瞳仁,日后他的假鼻子也要掉下。警察或许将在一个谁也提防不了的平淡秋天,从深宅大院抬出一具干皱的男性尸体。他的脸像被猫爪刨过很多次,地上飘着一张关注娈童案的旧报纸。
有些人根据这些细节,从自己平庸得可怕的身躯上发掘出源源不断的道德优越感。
可是上帝在人类面前总共只显过两次形,一次是在疯狂失控的美国码头,名字叫狄更斯;一次是在20世纪某日的演唱会上,名字叫迈克尔•杰克逊。上帝就长这个样子,半人半妖,换个又高又直的真鼻子就不是了,换个祖传正宗的真白人也不是了。
上帝丑陋而无可挑剔,人们对那些世俗标准的美忽然有了肥腻感。
那日,数万站立的人群(怀疑有将近十万),像是大风吹过的麦田,发出干渴的骚动声。在他们的眼前,有一片白炽光,像是隧道尽头的天堂景象,刺眼而茫然。忽然,那个非洲后裔像孙悟空一般,从石缝中嗷叫一声跳出,然后双手微微叉腰,头向一边侧去,像尖长的三角形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立着。那些肥的瘦的高的矮的麦秆,忽然消失了具体的现状,像炸开锅一般拼命向前伸出手来——好像洪水来了,他们就在自身不保的屋顶,好像所有的毒品都冲上脑袋爆炸。这个时候你塞给他们一个丁字裤美女,他们会踩死她,你塞给他们一张巨额支票,他们会吃掉它。他们开始向那些穿红色上衣的保安发起冲击,他们想摸到上帝的衣服,上帝如此之近,如此真切,却又如此遥不可及,他们撕开喉咙,毫无廉耻心地大叫。那臣服的喊声像是鸟群,忽然啸聚于天空,马上他们又醒过来,并在短时间内达成默契,开始整齐地叫着上帝的名字:杰克逊!杰克逊!杰克逊!
杰克逊站在那里,岿然不动,是个真正的统治者。希特勒或许还要用舌头和扩音器去舔群众的痒,在自己和人群间完成心理协商,但是杰克逊不需要,杰克逊只需要那样站着,谁也不理。台下所有人都傻逼了,傻逼得热泪盈眶。
两分钟后,上帝忽然把头一甩,就好似刀突然向所有人的心脏一划,尖叫声忽像闪电,猛然腾起,刺向天空。那些女子男子疯狂的不疯狂的,喊完了张开嘴无声地哭,那些眼泪像是河流,肆无忌惮地流下面庞,穿越衣服,汇聚到广场,那些眼泪被骚动的脚步踩得一文不值。可是谁在乎自己这点忧郁的财产呢?
有人甚至为此几乎要奉送出生命,保安和警察艰难地将窒息的歌迷传送出来,置放到担架,可是在担架上,那人的嘴巴却仍是在抽搐。就是这样死了,这人大约也不会知道自己死了。
内裤外穿的杰克逊轻轻摘下来墨镜,那些刚刚不相信他动了的,忽然摇头晃脑起来,他们重新任皮肤经历一次强烈的痉挛,他们不敢相信,他们捂上眼睛,再度摇头晃脑起来。他们觉得幸福不可抑制,他们像榨汁机一样榨着自己可怜的眼泪。
杰克逊走动起来了,像个机器人。然后他双手向两边一指,舞台两侧便同时爆出两颗烟弹。此后人们进入了持续的通灵时间,每个人都在这狂欢中获得了与上帝单独通话的体验。
这些人好似因为杰克逊而获取了生命。
这些人的心灵被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聪明抚慰。
这些人是心甘情愿的奴隶。
后来所有模仿杰克逊的人都失败了,没有人再能像他那样奴役最广泛的人群。
看看上帝20几年前还是黑色时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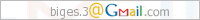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