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旗帜鲜明地歌颂土耳其
——————————————————————————————
在所有的尊重中,赢得敌人的尊重最难。
终场哨响,特里姆向勒夫道喜,这是失败者的风度。然后,比埃尔霍夫和他的同事们停止了欢呼,一起由衷地呱唧呱唧。
特里姆配得上对手送上的掌声。特里姆不用吟“恨不抗德死,留作今日羞”的励志诗,真爷们做事从不后悔从不装B。
比赛结束之前,土耳其的替补席上只有一个人,第三门将托尔加。赛前从土耳其帐中传出的消息是;由于人手短缺,若出现意外情况,特里姆将不得不派上候补门将托尔加司职中场。仅此一点,土皇帝就够格进入大师行列。大师,就是那种用土豆也能做出美味佳肴的人。
鞑靼语里,突厥意为勇敢,土耳其之意,就是勇敢者的国家。
上场的十三人,每一个都是嗜血的死士。特里姆说,假如比赛拖到加时,挺进决赛的未必是日耳曼人,而是突厥人的后裔。
这绝对不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场面话,如果不是“地精”拉姆,结果还真不好说。特里姆和他的弟子们惟一的失误,也许就是不该先进球,我的兄弟们此前曾经制作过这样一个标题:谁还敢领先土耳其人?
德国人只“敢”领先了八分钟,赛米赫就破了莱曼的门。但土耳其人的不幸,是遇到了比他们更不抛弃不放弃的日耳曼许三多,没有最一根筋,只有更一根筋——最不像德国人的拉姆用最土耳其的方式终结了土耳其逆子。
很古龙地总结如下——
这世上有两种人不可轻易撩拨,一是荡妇,二是德国人。前者太风骚,后者太弹簧。
这世上有两种人效率最高,一是音乐家,二是德国人。前者仅用七个数字和五条线就可以谱出无数的乐曲,后者莱因克尔有过中肯的评价:足球就是双方各出十一个人,九十分钟后,由德国人获胜的运动。
所以,梦游的克洛泽是可怕的,漏人的拉姆是可怕的,五星上将巴拉克下士是可怕的,你不知道克洛泽何时醒盹、拉姆何时和队友撞墙、巴拉克下士何时加星。
狂欢之后,勒夫的第一感觉或许就是后怕,然后是庆幸,他的战车并不比土耳其人的弯刀更有杀伤力。花样中年勒夫将在此役之后迅速成长,他应该感激特里姆,感激敌人跟他玩命——有土耳其这杯烧刀子垫底儿,德国人神鬼不惧。
阿拉贡内斯的斗牛士,希丁克的北极熊,谁都没有把握干掉德国人。后者是靠坚韧的神经吃饭的,而现在,德国人的神经又被土耳其人浇铸得盘条般又韧又硬。
再搬出帕慕克,土耳其人并不喜欢的诺贝尔作家帕慕克。
在《白色城堡》这部寓言中,一个威尼斯人和一个土耳其人越长越像,他们互相学会了对方的语言,甚至比对方更了解对方。之后,土耳其人逃离,以威尼斯人的身份隐居意大利;威尼斯人留下,以土耳其人的面目活在土耳其……
所 谓融合,曾在亚平宁执教的特里姆,和他打造的土耳其足球算一个案——以亚洲人的体魄,吸纳欧洲足球的精髓。足球和政体的脱亚入欧,土耳其人做出了再正确不 过的选择。总和高手过招,挨揍挨得多了,就有了打人的资本;老是跟臭手下棋,你一定会成长为臭棋篓子,这道理连我们街上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混混都明白。
1982年后的土耳其,政教分离,推进民主,小孩子上五年小学不需花一个里拉,穷人生病住院有国家医疗机构埋单——上学不用掏赞助费择校费,看病也不用倾家荡产卖肾卖肝,诺贝尔的遗产都能分一杯吃,更别说足球,无需思虑生活之艰难的孩子们,自然有踢球的闲心雅趣。
小小足球,与人种与政治与文化皆有关联。
你反驳可以,但是别再给我举1966年朝鲜1比0灭意大利进八强的例子了好吗?我还想给你讲伊拉克前足协主席、萨达姆家大少爷乌代先生用皮鞭激励该国球员的故事呢。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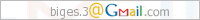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