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重新进入过去,状况类似于救火,能记录下来的财物有限。有时烧掉的废墟太难看,还需要进行拙劣的重建——无论怎样,从离开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对事情原貌的掌握。这就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
秋天通往郊外的柏油路,飞扬着枯黄的树叶,车内放着Nirvana的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这本是催情的好环境,但我却怎么也回不到往日的撕心裂肺了。我稳定地控制着方向盘,就像稳定地控制着家庭、生活和工作。我很难理解五年前的自己,为什么会抑制不住痛苦,要去送命。
无疑,当初我走上阳台,自有其理由。我应该是扔掉了电话,对人世最后的几步路程浑然不知(现在记起来,那地面应该是由黑黄色的地板砖铺成的,反射着下午浑噩的光芒)。我双手扶着低矮的阳台,只要猛然一个前倾,一切就结束了,我将头朝下,砸在六层楼的底下。那是痛苦的想象,颅顶将发出破裂的声音,这沉闷的声音很快传染到颈椎,最后无用的肉体扑倒在地,像懒惰的肥狗在下午的地面小憩。当时这个场景进入到我那还存活、还在运转的脑袋,但没有吓倒我。我相信有很多人这样吓回去了。我没有,我尽力告诉自己不是懦夫。但是这个时候,远在喀丘城镇的父母似乎出现在楼下,他们围绕着什么都没有的地面悲惨地叹息着儿子,他们甚至仰起欲哭无泪的面孔,给天空中的我观看。
这点恻隐之心救了我。后来我总是告诉别人,世上难做的事不是消灭自己,而是让一无所有的父母赶着马车,将支离破碎的儿子拖回到八百里外的乡下。我离开危险的阳台,走下楼,浑身颤栗地摸了一遍那可能坠至的地面。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成为父母的儿子,为父母而活,父母说结婚我便结婚,还生了儿子。我曾相信,等父母过世,我就可以结束自己了。但是父母死去后,我发现自己又不能成为妻儿的债务。我习惯了这种平庸而幸福的日子,我的妻子和和气气,儿子纯如白纸,我实在找不到痛恨生活的理由。
在我走上阳台前,应该是扔掉了电话。电话里响着对方挂机的声音。就表述空虚而言,再没有比电话更残忍的了,门关上了悄无声息,而电话会留下长久的嘟嘟声。正因为如此,我倍受嘲弄。我被蹿燃的愤怒和绵绵细雨般的委屈绑架,失去理智,快步走向阳台……真相应该是伪装成恻隐之心的怕死情绪,是那股怕死情绪又将我拉回人间。这真是丑陋的一幕。
在房间里,我的脑海持续闪现着和那个女人性交的场景,在当时,我感觉一切自然而然,疯狂激烈,像是有好多战栗的语言形容。但现在,我回忆起与她的性交,和回忆与别人的性交一样,都是简单的进入抽出,夹杂着一些床铺和喉咙的声音。如果有耿耿于怀的,就是她窄小的阴道,和窄小的内裤。我相信,就当时而言,我准确地体验到性与爱的一体,在性交结束后,我开始裹挟着她生活,像是双头娃娃。我觉得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女人。
但是在三天后的电话筒里,她活活割走了我身体内的她,她野蛮地取消了我继续靠近她的资格,弄得我血肉模糊,难以苟活。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这本来是段艳遇,但是我却持续感恩于爱情的挛缩。我看到摇晃的瘦弱躯体,和每一寸皮肤里埋藏的衰老。像看到就要熟透的苹果,挂在春天的新枝,我看到就要衰老的面容,挂在年轻的躯体,我听到她说“你会不会嫌弃我的衰老”,我准备说“我热爱你的衰老”,被封住了嘴。我充满了悲悯的感情。但是三天后,就是她设置了没有温度的冰川,我很快得到一切,又很快失去一切。我陷入到这大喜大悲中,像赔本的赌徒,在下午的房间里任风吹过单薄的身体。
轿车向着秋阳的深处开,村庄还留了些绿色的内容,路边的草坪则已枯黄。我将车停在路边,抄近路走到了公墓。我用了不到五分钟就找到5023号墓碑。它和5022、 5024号没有区别,只是一块凿下的石块。5024之后没有新的墓碑了,这说明5023号死得不久,你看碑上的字不是还很稚嫩么。
我抽了一根香烟,一遍遍读墓碑上的文字:“夜莺还年轻,但衰老还是来临了”。这应该是莫斯科一个独身女人写的诗。

上面是我死去的躯体 下面是我活着的灵魂 你可以看见 只是需要一面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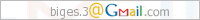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