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日星期一
也说女人的발
关于《太阳照常升起》
自古以来,受所谓评论人喜闻乐见的作品都有个共性——涵义不确。比如《一条安达鲁狗》(整部片子里没一条狗)。比如《精疲力竭》(“他说什么?”“婊子!”)。再比如《太阳照常升起》(“我恨!我恨我恨我恨!我恨!”)。
有人从《太阳照常升起》中读出了女人的脚,这我不佩服,我也不是瞎子。但又有人读出了“鸡巴的力量是多么伟大”,这个,我就很佩服了。被评论者们看为《红楼梦》一般的《太阳照常升起》,是张开了双臂欢迎一切索隐派的,无法从女脚中解读出反女权主义的马脚,完全是我功力不够。如果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解码,我很可能只能将这部电影翻译成下面这个样子:
这是一部无限夸大女权主义,女性膜拜严重的影片。
影片分四段。在开头,“银幕上也出现了一双女人的脚,干净,柔嫩,脚趾甲修剪得干净整齐。”然后,摄影机随着这双脚跟拍,阅读着它走过的泥土和草地。作为一个隐喻,导演用这个审美倾向严重的镜头告诉观众,我的视角就是女性的脚,请跟我来。
在第一段故事中,周韵扮演了一个美丽的近似于巫师的通灵人物,在扇了她的儿子——男主人公房祖名好几千个耳光,并把他折腾得五迷三道后,周韵消失了——她的消失使人想起白日飞升。小溪中,周韵的衣服和鞋子呈尸体状随波逐流,宛如奥菲利娅。肉身的神秘失踪代表着导演对女性形象的神化倾向;事实上,“疯子”这一身份已经隐含了神性(我就这么一写,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福柯专著《疯癫与文明》寻找科学根据)。
第二段故事中,黄秋生首先作为一个青春美的守护者出现;无意中摸了一把女人屁股后,在落荒而逃中摔断了腿——这是他对女性美所做的第一次献祭。随后,在陈冲和另一不记名女性对其表达了热烈爱情后,他在恐惧迷惘慌乱焦灼幻灭等复杂情绪中自缢身亡。风格清新的电影语言以及有意夸大的女性肉体美都在暗示观众,黄秋生是摆在女性祭坛上的口唇期祭品(我就这么一写,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弗洛伊德有关论文寻找科学根据)。
第三段故事中,被扇了几千耳光的房祖名再现江湖,这一次他以闷骚细腻战胜了肩挎猎枪的猛男姜文,在周韵留给他的石头房子里将姜文的娇媚老婆搞上了床,最后死于姜文的枪口下。这一段故事中,导演运用热烈飞扬的电影语言大肆讴歌性的力量——是什么把姜文从田野里呼召到北京又呼召回来呢?是女性的肚皮。而房祖名在抵达生殖期后,终于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熟,最终死而无憾;虽然他为之而死的女人看着丈夫从北京带回来的大口罩依然笑靥如花。
第四段故事:非叙事空间。两个骑在骆驼背上的女人在诉说中带领观众走入导演的狂想,也走入这部电影的源代码。路的尽头,姜文与他的新娘终于会合,在狂欢中安抚着整个沙漠的焦渴;而周韵在日出时分奔跑的火车上生下了她的婴儿。影片结束在对花丛中的婴儿的深深凝视中——这是这部电影的本源,也是人类的本源:万般归宗,回到初民纯净的生殖/女性崇拜(我就这么一写,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我的千岁寒》寻找科学证据)。
恕我直言,单纯从作品出发揣测作者对女性的态度是十分笨拙的。比如在《动物凶猛》中疯狂意淫丰乳肥臀的王朔,现实中很可能只迷恋平胸无臀且努力知性的清纯女星。而张艺谋的口味也很难从他的电影中觅到端倪:《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众多女性对一个半衰男人的性机会展开争夺;《菊豆》中,处于弱势的男人企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独占得到父权;《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野合被宏大叙事化为民族赞歌;《我的父亲母亲》中,所有的角色都回到儿童期的无性状态,唱首山歌给妈听......除了群交,苟合,乱伦就是阉割;其实我觉得,张艺谋本人除了择偶标准趋近丫鬟化,还基本算是热爱正常妇女。
再说两句昆汀他轮替诺。这个电影怪才+顽童也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的标本。在他的电影中,人物和情节都是棋子,任他摆弄,无论是没有男人的DeathProof还是没有女人的水库狗——KillBill中的女主角选择也许不过是因为昆汀实在喜欢乌玛瑟曼。当然,如果一定要寻找科学证据的话,《低俗小说》中的女出租车司机难道不能被称为亮点?请问有何深度叙事意义?《Jackie Brown》中到底是男人帮了女人,还是女人帮了男人,还真难说。
说到“对待女人的态度是渐进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是崔健。早期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女性形象在崔健这里是个单纯的符号:柔弱,善良,美丽,但是阻碍着奔向混沌理想之路的脚步:“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拒绝花的迷香...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可是我发现我已离不开你,姑娘”,“我感觉我要喝点水/但你的嘴将我嘴堵住”,“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说你爱我”;而到《红旗下的蛋》,女性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我要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我要告诉你一切但不要你生气”,“一个姑娘带着爱情来到眼前/像是一场风雨吹洗着我的眼”;《无能的力量》中,女性已经完全以独立的,富有精神力量的姿态出现:“你说干就干/走得更快/象天使一样飞来飞去/你的视野开阔/而我的窄...我只会吹还不会骗/天空太黑灯光太鲜艳/我已经摸不着了北/请你别离我太远/只有你能够/让我感到体面”,“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孤独的姑娘/检查一下我的心里的病是否和你的一样...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坚强的姑娘/也许你比我更敏感 更有话要讲/你会相信我吗 你会依靠我吗/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我总觉得说到一个种群,问出“如何对待”这种问题,本身就已经隐含了将其视为弱势的倾向。“如何对待同性恋?”,“如何对待有色人种?”,“如何对待农民工”?无非象对待你自己一样,何须问?男人,女人,都是人,任何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都应该得到尊重,何须问!
女人没有小鸡鸡,这是事实,但不是残疾,何须男人扶持着学习站着撒尿——正如男人间互相辱骂“傻逼”之前,完全无须先为对方造一个逼。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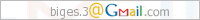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1 条评论:
Shino 说:
你觉得姐弟恋有普儿么
叶三 说:
有,别是亲的
Shino 说:
废话
叶三 说:
你怎么了,爱上小弟弟了
Shino 说:
别用 爱 字
Shino 说:
哪儿到那个地步啊
叶三 说:
好吧
叶三 说:
喜欢上小弟弟了?
Shino 说:
别用 喜欢上 哪儿到那个地步啊
叶三 说:
我操
叶三 说:
想操小弟弟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