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世界需要一个球
有人正沉浸在漫漶的悲伤之中,有人正在醒来,在某张床上,准备咧开嘴笑。你不能说,世界就是这么操蛋世界就是这么健忘,健忘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好东西,上帝不忍看着他的子民深陷于忧伤的泥沼之中,于是上帝说要没心没肺,就有了没心没肺。
一只空心的皮球是没心没肺的,它正破空而来。板结的、沉郁的、愁苦的世界需要它。
当罗比尼奥皮雷们举着一张写着“今天我是四川人”的横幅时,当一袭白衣的托雷斯垂首祈祷,默念着“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时,不安分的足球停止滚动,那些渺远的生灵,让世界阒寂。足球表达了它的哀伤,观者的情绪被感染,一些老爷们的思维回归常识:命大于球、命大于运。世界是平的,世界是长而且平的,而痛感的路线是枝蔓状的,就如那几夜人们血丝密布的眼球。因此每一次痛感都能传导至每一个角落,关山万重不可阻。
能阻遏痛的,只有时间。
丘吉尔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有两种:爱上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持久的忧伤就是一面倒向自己的墙,这样痛苦不堪的攀爬,结果必然是被悲伤压垮。幸好还有时间,时间会提醒生者,放下悲伤,开始重建——重建家园、重建心绪。生者需要摆脱需要平静,需要哪怕瞬间的快乐来间隔林密的忧伤,甚至,需要喝几瓶酒,需要看几场球。托雷斯们在地球仪上指不出的四川正在康复,那个从废墟中被救出来的男孩,第一个要求是可乐,冰冻的可乐,川人的通达不可低估,也许那个孩子现在的要求,就是在帐篷里看C·罗踩着“单车”连过数人之后进一个球。受难者需要娱乐,在祸灾渐远的时候,在那些帐篷学校里,电视、书和玩具熊,哪怕一只皮球都胜过一个连的心理学家,胜过一车皮的文学大师。
遗忘和眼泪一样,同是人类的必需品。眼泪是疏浚悲伤之用,这种液体可以保证我们避免精神之洪的崩溃。遗忘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我怀疑大脑中有一种物质,会在它们的主人遭遇大恸之后释放出来,冰冻、麻痹某些记忆细胞、进而稀释悲恸。这种物质是上苍赋予的,于是我们看到伊拉克少年赤脚在战后的废墟踢球,看到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新奥尔良某个无名小镇上竖起的篮球架,看到汶川的残垣断壁旁做游戏的孩子。
有些东西是炮火和灾难不能摧毁的,比如自由,以及自由的衍生品——快乐地享用短暂的人生。不过遗忘不是压抑,更不是受迫性的压抑,没有人有权力命令别人 “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规劝也不行,因为你不是受难者,他们的凄苦无关你的福祉,他们的苦难并没有让你秋风秋雨愁煞,只有受难者自己才有选择遗忘、或者记忆的权力。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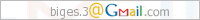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