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3日星期四
天涯何处无芳草
是熙宁4年吧,千年不忘的熙宁4年。
我在西湖边的教坊里,不知不觉已是经年。那天,春日正好,嬷嬷叫我们:“孩子们,准备上场了。”于是,我盛装和姐姐们歌舞。我最小,歌声婉转如雏莺出谷,舞姿曼妙似随风杨柳。小巧如我,也能赛过飞燕做掌上舞。艳服里,是瘦小的身体,浓妆下,是无邪的眼睛。我还是个孩子,12岁。
宾客中有你。我不知道你是谁,姐姐们都羞答答地看你,谈论你,他们说你是“大学士”,一等一的才子。你青衫磊落,星目朗朗。你的眼睛那么亮!你那么亮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很久以前就熟识。你的朋友很多,你们说笑,唱和,我流转的清波看到你时不时瞥向我。
舞罢复宴饮。我洗尽铅华,素面来见你们。自这一刻起,你的眼光就牢牢锁定在我身上。你的朋友们让你赋诗,你看着我欣然口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哄然,他们笑了。而我,欢喜,又懵懂。你有很多女“粉丝”,高贵娴雅的富商夫人为你抚琴以求一诗,更有惠州的温超超日日徘徊在你的窗下听你吟诗作赋,未得你的眷睐以至郁郁而终。你是为他们写过诗词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做,你就为我留下的千古华章。
后来,不知道是谁为我赎了身,又把我送到你府上。我就成了你身边的一个伺女。你和夫人对我好极了,你们教我诗文,我为你们歌舞、铺纸、研磨。再后来,我从一个卑贱的歌姬,成了你的“如夫人”。
大夫人亡故很多年了。夫人在陪伴你26年之后,也离开了你。我比你小那么多,以为可以先送走你,可还是走在了你前头。“几世修得死夫前”,我们该是怎样的造化!生即嫁了你,死又得到你情深意重的眷恋!
看过你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夫人不吃醋,我更不会吃醋。一个为亡妻栽下3万株松柏的男人,一个在死去十年的亡妻坟前凄惶落泪的男人,是如此豁达明亮而又九曲回肠,这不正是自己期盼的终身所托吗?人人说你风骨刚硬,他们哪知你的似水柔情和清隽疏秀?
夫人是大夫人的堂妹,她仰慕你多年,做你的续弦,也不觉得委屈。这26年,她陪你几度沉浮,终于在又一次罢黜之后,于颠沛流离的途中撒手。你答应她:“死则同穴。”她们都走了,只有我还在。我没有想过我会先你而去,所以,我牢牢记住你对夫人的庄严承诺。谁知……
还记得那个深秋,月凉如水,清霜满地。凄冷的风吹着堂前的灯烛,忽暗忽明。你说:“朝云,为我唱一曲《蝶恋花》吧。”我不觉落下泪来,咽不成声。你问:“为什么哭泣?”我谎道:“伤春。”你笑了:“我在悲秋,你却伤春。”你笑了,我心安然。你一直夸我是“解语花”,难道我真的和你没有了灵犀?“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里面有多少旷达与伤感!你不该受此磨难啊,我岂是伤春,泪为你流……
后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我走了。子瞻,终我一生,我没有这样叫过你,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兄长,是我的恩人,是我一生引为骄傲的人。我是一直叫你“老爷”的,现在,我走了,才这样叫你。我爱你吗?千年以后的人喜欢说“爱”,可我不懂。我只知道,和你在一起,就是满心欢喜。这样一个横绝千年,天资卓绝的男人,能跟随你生死相依,是不是刻骨铭心的“敬”和“爱”?
曾经的如花美眷,经过似水流年,都付与了断壁残垣。那又如何?自我走后,你再也不忍卒听《蝶恋花》;自我走后,你葬我于惠州西湖,“六如亭”的晓风残月,伴我岁岁年年。是你对我深深的想念?我知道的,我懂。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在对的时候,遇到了对的人,叹一声:“呀,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们没有错过,没有阙如的深情,没有怨恨和遗憾。天涯芳草无穷尽,此爱绵绵无绝期——我是你永远的朝云。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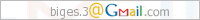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