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神话、意见领袖及其它
1、事件、经历和神话
事件、经历和神话,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唤醒过去,实质都建立在对史料的不同体验之上。
事件,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力求客观的叙述,目的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经历,即各个不同层面的人拥有的思想、产生的感觉以及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的巫术、谣言、狂热和地方军事扩展,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前述要素包括义和团运动本身,均是一种经历。
经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它们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并且成为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推荐阅读: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2、群体与意见领袖的“模仿循环”
当领袖们打算利用观点与信念来影响、支配群体时,通常有三种重要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或者将推理肤浅化、将证据预设化),是征服群体头脑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我就说你是傻逼,绝对不证明你是傻逼。因为严谨的证明过程会相当漫长、枯燥、艰涩,群众没有耐心也没有体力去追随。老毛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决不屑于论证“为何反动派是纸老虎”。与此类似的还有全球通广告语“我能”,以及奥巴马对此的改译“yes we can”。
但是,如果没有不停地重复断言,影响可能转瞬即逝。拿破仑曾说,最有效的修辞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从《诗经》到脑白金,都相当明白重复的力量,前者因而流传百代,后者因而风靡一时。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有效重复,而在此种重复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沉默的螺旋”)而不存在异议,或者反对声音微弱如垂死者的呼吸,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亦于此启动。
有大众的流行意见,也有小众的流行意见。前者譬如“抵制法国货是爱国的正义之举”,后者譬如“杨佳是英雄”。这些意见在混乱的头脑中极易流行,因为头脑混乱就如疯狂一样,极易传染。在精神病医生中,不少自己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据说有些疯病甚至可以由人传给动物,比如广场恐惧症。
传染在大多时候又是通过模仿进行的。人们会不知不觉模仿意见领袖的言行,而在潜意识中,则多半藏着通过模仿而得到或分享意见领袖的成功的渴望。
意见领袖的成功,来自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即所谓名望。值得注意的是,与流行意见相似,名望同样也有大众与小众之分,恕不举例。现实中,名望对其受众群体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是卓著的,可能麻痹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充满惊奇和敬畏。而这惊奇和敬畏所指向的对象,却往往只是名望本身,而非名望背后的真实个体及观念。
在被模仿的同时,意见领袖也不得不模仿或者重复自己之所以被模仿的东西。他曾经制造的公众观念,即使随着时光流逝而在自己心中有所改变,也很难大声讲出来。因为如果这样做,追随者模仿起来就会过于困难,甚至由此产生怨气,站到他的对立面去。
由于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模仿循环”(作者生造的一个词儿),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就极易造成言论、价值观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乃至行为的高度相似。在大众圈子内,人们因相似而获得认同,进而产生安全感;在小众圈子里,人们相互抱着取暖,因小群体中的相似而获得“我道不孤”的自信,又因与大群体的不相似而获得“遗世独立”的骄傲。
大多数意见领袖的悲剧在于,不管他们如何讴歌群体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群体运动中,意见领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骗者。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和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要求更多的自由与更大的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象那些响应者,也渴望同样的东西。然而,响应者们真正渴望的也许不是意见领袖呼吁的自由,而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的自由,进言之,他们要的也许不过是建立在空洞概念、狂热标语、激进思维基础上的另一种统一信仰而已。托克维尔的话尖锐到残忍,但并非全无根据:“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一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叶芝诗歌中描绘的图景很可能就降临大地,甚至已经降临:“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推荐阅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3、在群体运动中,恨比爱更有力量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群体运动都满带戾气,与暴力同行。因为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令人聚结在一起的胶水中,最好用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再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几乎所有利用群众运动起家的专制者,都相当擅于利用仇恨的力量。曾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他答道:“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创造一个新的‘犹太人’……关键是要树立一个具体的敌人。”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在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推出一个接日本人班的新魔鬼,却被共产党树立成了新魔鬼。
恨为何有如此凝聚力?很简单,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通常不会寻找同好,甚至会把同好视为情敌。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志同道合者,所谓“与子同仇”。
奇怪的是,我们的恨意常常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更奇怪的是,我们释放出的恨意也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却常指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对象。譬如,长期被意识形态洗脑现又身处经济萧条巨大压力下的中国青年,轻易就被煽动,走上街头,去抵制法国货。
在充满恨的群体中,个体又常常会失去个人责任与个人目标,成为“无名氏”,或者实验器皿酿造的漩涡中的草履虫。而随着无数个体的身份与责任感的丧失,又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众运动的狂暴,使漩涡越发巨大。
消除群体戾气有一个好办法——让其中的个体重新发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及相应责任。
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被拍成经典电影)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一群南方白人聚集起来,要对一位被误判为强暴犯的黑人罗宾逊处以私刑。罗宾逊的律师阿蒂科斯站在暴徒前面,矛盾一触即发。这时,阿蒂科斯8岁的小女儿走到人群当中,偶然认出其中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并跟他聊天:“你还记得我吗?坎安宁先生,我是路易斯,有次你给我们带了山核桃,记得吗?”起初,那个叫坎安宁的先生及人群都没什么反应,小女孩就继续谈笑。忽然,坎安宁蹲下来,拍她的肩膀,说:“我会代你向我儿子问好”,接着站起来,大手一挥:“我们散吧!”他叫着:“回去吧,朋友们”。
小女孩无意的举动——叫出一个人的名字,跟他拉家常,使他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发生改变,进而促使一群高度“去个体化”、无法辨认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群市民的集合。最后,这帮重新找回姓名的人没有实施任何暴行就解散了。
(推荐阅读:阿伦森《社会心理学(第五版)》)
4、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另一种诠释
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存在限制,而是指不存在有害的限制。
人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只能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一刀切的人人平等,否则就是人民公社。
平等与自由不是一码事。平等是表示关系的词,自由是表示否定的词。很多时候,自由与平等不但不是一码事,还是相对立的两个东西。
詹姆斯.斯蒂芬认为,法国人爱全人类的方式,也即所谓博爱,是他们众多最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一。詹姆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其后任是阿克顿),终身致力废除奴隶制并最终看到废奴成为现实。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不是泛泛而谈的博爱,而是冷静的思想:“能够要求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与正义”。事实上,他认为博爱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最多是宗教信仰或者“伪善俱乐部”的教条。
(推荐阅读: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
5、托克维尔的预言
“如果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想想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以及1986年后的台湾,托克维尔在1856年的预言颇足玩味。
他还说了这么些犀利闪亮的话,虽然略带点儿贵族精英感: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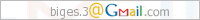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2 条评论:
古代一个丫鬟,偶放一屁,恰好被主人听见。主人以为放屁不雅观,非要打丫鬟的屁股。当主人看到丫鬟的美白的皮肤后,便把丫鬟给强奸了。一天,丫鬟又来找主人。主人问:“何事前来?”丫鬟说:“我又想放屁了。”被强奸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一个丫鬟为何从被迫强奸发展到了主动送奸?显然是被强奸的快感在作怪。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小偷去一家偷东西。发现女主人在裸睡,于是,淫心大发。女主人一阵挣扎,小偷以为要喊人。十分惊慌。不料,女主人却说:“贼哥哥,你是什么时间来得。”
一位智者说:“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多次是夫妻。”很多人在第一次被强奸时,感到痛苦。可是,几次被强奸后却成了夫妻。可见,强奸带给的快感,是一种神气的力量。一个宫女被齐桓公强奸,这对于拔腿无情的帝王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得到快感的宫女来说却耿耿与怀的大事情。齐桓公老年,被人用围墙围困。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个宫女爬过围墙,来到他的身边。齐桓公问宫女:为何对自己这么好?宫女说:“我就是那个被你强奸过的宫女。”类似宫女“一日被奸百日恩”的现象,在生活决非个别现象。
强奸带来快感,在生活中是很正常的事情。生活就是充满神奇,当一个人或一群人第一次被压迫时,可能大喊大叫,难以忍受。可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屡屡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长期被压迫,产生被压迫的快感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压迫人民一次的是贼,如果长期或一贯压迫人民的人,却会成为最受爱戴的大救星。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乌克兰在三十年代初付出了一千一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在1936年到1941年的大清洗恐怖浪潮中共有七百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两千五百万人,甚至可能达四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成了一个残忍、暴戾而又极富组织能力的暴君之手。可是,在莫斯科省的一个区党代表会议,会议进程中每次念到斯大林的名字,所有代表都一跃而起,高喊“乌拉”。会议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时,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几分钟过去了,场面依然是欢呼依旧。人们的手掌已经发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然而谁也不敢第一个停下来。
如果想要一个或一群人听话或癫狂,强奸的办法比协商的办法更让人产生快感。一次整人就是一次强奸,而多次强奸比一次强奸带来的快感更多。萨达姆上台后,在一次清洗反对派的大会上,每当念到一个被清洗者的名字,会场就是一次雷鸣般的掌声。清洗一个,一片欢呼。当清理结束后,整个会场成了狂欢的海洋。独裁政治就是这样,人们一次次被清理,就是一次次强奸。快感随着被奸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强烈。一个统治者成为他们的暴君及精神领袖之后,整个国家也就成了快感的海洋,高潮的世界。
朝鲜金家王朝,可谓现代社会的一大恶魔。可是人们却把他比作慈祥的父亲、伟大的领袖、舵手、统帅、红太阳。有一次,朝鲜体育代表团到韩国参加比赛,金正日的照片在韩国街头遭雨淋湿后,恰好,为朝鲜的美女啦啦队成员看到。为此,她们失声痛哭,并强烈抗议韩国政府的侮辱行径。30~40个美女跑到宣传横幅前,表示强烈地抗议。一路上,她们高举着金正日的照片,一边如丧考妣。看到北韩美女助威团大声哭喊,一个过路人形容她们“就像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
人一生难免不被强暴,被歹徒强暴,我们往往能感觉强暴。可是对于强权强暴,人们往往先是痛苦、继续麻木,只好可能发展到快感。这让我想起一个幽默。一个女文工团员结婚后,在新婚之夜,军官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了。丈夫很气愤,非要去跟强暴妻子的人算帐。女文工团员只好说出了她和几个姐妹轮番服务伟大领袖的事。作为军人的丈夫马上从床上爬下来立正说:“向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敬礼!”
“绿帽子”也能给被强奸者家人带来快感。这是痛苦、麻木之后的必然。在一个时时被强奸的社会,被强奸的快感也是一种极易传染的疾病,让被强奸者的家人也要分享一下快感的传递。在封建社会,大臣受罚,要对皇帝心存感激,即便被杀,临死还要谢主隆恩,高喊“吾皇万岁”。至于家人痛苦、麻木之后,必须在“吾皇圣明”快感之中才能寻求出路。
压迫就象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摆好姿势享受快感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在“要么被杀,要么闭眼”的现实中,把屈辱转化为快感不失为一种摆脱的方法。在一个痛苦、屈辱而又无助的现实中,我们常常被人强奸。在被强奸的快感作用下,我们成了一个自觉的、恬不知耻的助奸者。
鲁迅说:“如果从奴才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强奸之下,奴才不仅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还能在极致的奴才生活中体验到被强奸的快感
顺从者比强奸者更可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