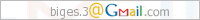|
| 发件人 Biges.3-02 |
2009年7月3日星期五
2009年1月1日星期四
It's All Bullshit !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2008年最后一贴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大多数年终盘点的背后,都藏着对死亡的恐惧。日子跟人一样,都要死掉,譬如今天一过,2008年就死掉了。于是各种盘点、回顾、总结粉墨登场,为死去的这年唱一曲真诚或虚伪、睿智或弱智的挽歌。
或许又可以这么说,在大多数年终盘点的背后,都藏着对过去的珍视。而这种珍视本身,即是对死亡之恐惧的另一面。如布克哈特所言:人类精神常自带原动力,必须把它对各种经历的回忆转化为自己的财产,否则就极易空虚且缺乏信心;过去的欢乐和悲伤无穷无尽,我们必须从中获得理解能力。
但理解过去谈何容易,无论你如何谨慎,在审视过去时总难免过滤一些东西,又虚构一些东西。最后你所看到的过去,很可能只是你想得到的过去,而非过去本身。
所以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干脆选择不回忆过去,而是将目光向前看,投向这个时代。
然而,概括一个时代,尤其是身处其中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鱼说不出水库的容积,蚂蚁看不到离蚁巢1000公里外的米粒。
概括或不可行,聚焦是可能的。
在2008年,我所关注的两个时代焦点,就是“国富民穷”与“群体事件”。
1、关于国富民穷,有两篇好文推荐。
一篇是丁学良的《如何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点此进入),在分析现状上,丁文相当出彩,在改变现状的建议上,则略显乏力。
丁文将中国经济的现状概括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些断言建立在三个不同研究机构的成果之上: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
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 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 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一篇是陈志武的《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清晰有力。(点此进入)
“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 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2、关于“群体事件”,《南风窗》最近的报道《2008年恶性事件密集发生 官民矛盾步入显化阶段》值得一读。(点此进入)
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提法,颇具启发:
“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诸多事件中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激活。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一些地方群众的不满并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早在2006年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危险性在于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即可,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确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上至部委层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任何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变得艰难而漫长,在众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间达到平衡。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当改革的获益被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谋瓜分,无数明显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被粉饰,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沉默中累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已成共识却难以短期解决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近10年来陆续出台,近年民告官获胜的案子也已并不鲜见,但毕竟只是少数,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无法立案或者以败诉告终的情况,而即使小民胜诉,也存在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况。
作为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特别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官与民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而调查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导者,那么民众的不满将有多大?
社科院的报告也认为,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营企业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官员的社会形象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一旦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众质疑,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无直接利益冲突会日益增多。而官员在实际施政中的失当、不当甚至违法,就直接加剧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好了,文章就推荐到这里。2009年一切会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谁都难下断语。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它会变得更好。今年8月以来,我的MSN签名档是“2008年,赶灾年,人们带着遗忘,匆匆忙忙,赶往下一个灾难”。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过消极,如果每个人都带着这种悲观乃至绝望,那么结局很可能就是悲观乃至绝望。就像社会学家托马斯说的,“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为真”。
乐观一点,我们可能会不断失望,但不会永远失去希望。
最后,在2008年的末尾,请允许我借用林志玲甜美的嗓音祝福大伙儿:
“新年快乐!2009年,加油啊,站起来,站起来”。
【附录】
2008创造社精华文章推荐(按时间先后顺序)
1、小说类
2、文史类
3、时评类
4、随笔类
2008创造社被和谐文章存目(多数可用百度或谷歌快照找到)
《冉匪又出事了》 2008-12-28
《冉云飞:平安夜不平安(转)》 2008-12-25
《为杨佳默哀》 2008-11-26
《绵阳三台人体炸弹案》 2008-10-21
《惊爆黑幕:三聚氰胺奔袭饲料业!》 2008-10-19
《哈尔滨的罗生门(转)》 2008-10-16
《哈尔滨事件延展:李清晨的得与失》 2008-10-16 1
《哈尔滨警察殴毙大学生视频流出》 2008-10-15
《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 2008-10-13
《胡 佳未能获奖》 2008-10-10
《香港媒体拍来贺电》 2008-10-9
《冲杯奶粉给党喝》 2008-9-19
《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转)》 2008-9-16
《三鹿的脱罪链条》 2008-9-12
《我敢打赌今夜一定有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 2008-8-8
《岂止一个杨佳》 2008-7-8
《把人民群众当SB》 2008-7-8
《中国仇恨》 2008-7-2
《周曙光独闯瓮/安的背后》 2008-7-2
《贵州日报含泪报道瓮/安事件》 2008-6-30
《这些链接目前还能打开》 2008-6-30
《谭力:总书记和总理来了,当然要笑》 2008-6-12
《“刁民”来信》 2008-5-8
《南都:彭州石化民间质疑》 2008-5-7
《浅薄令人震惊!令人发指!》 2008-5-5
《成都五四游记》 2008-5-5
《当地的拆迁村民是幸福的!》 2008-5-4
《关于彭州乙烯项目之“法律帮助”》 2008-5-4
《关于彭州乙烯项目之“达人建议”》 2008-4-30
《关于彭州乙烯项目之“望达人指点”》 2008-4-29
《关于彭州乙烯项目之“绝不收声”》2008-4-28
《关于彭州乙烯项目》 2008-4-26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神话、意见领袖及其它
1、事件、经历和神话
事件、经历和神话,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唤醒过去,实质都建立在对史料的不同体验之上。
事件,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力求客观的叙述,目的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经历,即各个不同层面的人拥有的思想、产生的感觉以及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的巫术、谣言、狂热和地方军事扩展,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前述要素包括义和团运动本身,均是一种经历。
经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它们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并且成为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推荐阅读: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2、群体与意见领袖的“模仿循环”
当领袖们打算利用观点与信念来影响、支配群体时,通常有三种重要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或者将推理肤浅化、将证据预设化),是征服群体头脑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我就说你是傻逼,绝对不证明你是傻逼。因为严谨的证明过程会相当漫长、枯燥、艰涩,群众没有耐心也没有体力去追随。老毛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决不屑于论证“为何反动派是纸老虎”。与此类似的还有全球通广告语“我能”,以及奥巴马对此的改译“yes we can”。
但是,如果没有不停地重复断言,影响可能转瞬即逝。拿破仑曾说,最有效的修辞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从《诗经》到脑白金,都相当明白重复的力量,前者因而流传百代,后者因而风靡一时。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有效重复,而在此种重复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沉默的螺旋”)而不存在异议,或者反对声音微弱如垂死者的呼吸,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亦于此启动。
有大众的流行意见,也有小众的流行意见。前者譬如“抵制法国货是爱国的正义之举”,后者譬如“杨佳是英雄”。这些意见在混乱的头脑中极易流行,因为头脑混乱就如疯狂一样,极易传染。在精神病医生中,不少自己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据说有些疯病甚至可以由人传给动物,比如广场恐惧症。
传染在大多时候又是通过模仿进行的。人们会不知不觉模仿意见领袖的言行,而在潜意识中,则多半藏着通过模仿而得到或分享意见领袖的成功的渴望。
意见领袖的成功,来自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即所谓名望。值得注意的是,与流行意见相似,名望同样也有大众与小众之分,恕不举例。现实中,名望对其受众群体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是卓著的,可能麻痹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充满惊奇和敬畏。而这惊奇和敬畏所指向的对象,却往往只是名望本身,而非名望背后的真实个体及观念。
在被模仿的同时,意见领袖也不得不模仿或者重复自己之所以被模仿的东西。他曾经制造的公众观念,即使随着时光流逝而在自己心中有所改变,也很难大声讲出来。因为如果这样做,追随者模仿起来就会过于困难,甚至由此产生怨气,站到他的对立面去。
由于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模仿循环”(作者生造的一个词儿),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就极易造成言论、价值观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乃至行为的高度相似。在大众圈子内,人们因相似而获得认同,进而产生安全感;在小众圈子里,人们相互抱着取暖,因小群体中的相似而获得“我道不孤”的自信,又因与大群体的不相似而获得“遗世独立”的骄傲。
大多数意见领袖的悲剧在于,不管他们如何讴歌群体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群体运动中,意见领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骗者。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和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要求更多的自由与更大的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象那些响应者,也渴望同样的东西。然而,响应者们真正渴望的也许不是意见领袖呼吁的自由,而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的自由,进言之,他们要的也许不过是建立在空洞概念、狂热标语、激进思维基础上的另一种统一信仰而已。托克维尔的话尖锐到残忍,但并非全无根据:“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一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叶芝诗歌中描绘的图景很可能就降临大地,甚至已经降临:“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推荐阅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3、在群体运动中,恨比爱更有力量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群体运动都满带戾气,与暴力同行。因为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令人聚结在一起的胶水中,最好用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再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几乎所有利用群众运动起家的专制者,都相当擅于利用仇恨的力量。曾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他答道:“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创造一个新的‘犹太人’……关键是要树立一个具体的敌人。”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在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推出一个接日本人班的新魔鬼,却被共产党树立成了新魔鬼。
恨为何有如此凝聚力?很简单,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通常不会寻找同好,甚至会把同好视为情敌。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志同道合者,所谓“与子同仇”。
奇怪的是,我们的恨意常常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更奇怪的是,我们释放出的恨意也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却常指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对象。譬如,长期被意识形态洗脑现又身处经济萧条巨大压力下的中国青年,轻易就被煽动,走上街头,去抵制法国货。
在充满恨的群体中,个体又常常会失去个人责任与个人目标,成为“无名氏”,或者实验器皿酿造的漩涡中的草履虫。而随着无数个体的身份与责任感的丧失,又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众运动的狂暴,使漩涡越发巨大。
消除群体戾气有一个好办法——让其中的个体重新发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及相应责任。
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被拍成经典电影)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一群南方白人聚集起来,要对一位被误判为强暴犯的黑人罗宾逊处以私刑。罗宾逊的律师阿蒂科斯站在暴徒前面,矛盾一触即发。这时,阿蒂科斯8岁的小女儿走到人群当中,偶然认出其中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并跟他聊天:“你还记得我吗?坎安宁先生,我是路易斯,有次你给我们带了山核桃,记得吗?”起初,那个叫坎安宁的先生及人群都没什么反应,小女孩就继续谈笑。忽然,坎安宁蹲下来,拍她的肩膀,说:“我会代你向我儿子问好”,接着站起来,大手一挥:“我们散吧!”他叫着:“回去吧,朋友们”。
小女孩无意的举动——叫出一个人的名字,跟他拉家常,使他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发生改变,进而促使一群高度“去个体化”、无法辨认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群市民的集合。最后,这帮重新找回姓名的人没有实施任何暴行就解散了。
(推荐阅读:阿伦森《社会心理学(第五版)》)
4、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另一种诠释
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存在限制,而是指不存在有害的限制。
人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只能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一刀切的人人平等,否则就是人民公社。
平等与自由不是一码事。平等是表示关系的词,自由是表示否定的词。很多时候,自由与平等不但不是一码事,还是相对立的两个东西。
詹姆斯.斯蒂芬认为,法国人爱全人类的方式,也即所谓博爱,是他们众多最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一。詹姆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其后任是阿克顿),终身致力废除奴隶制并最终看到废奴成为现实。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不是泛泛而谈的博爱,而是冷静的思想:“能够要求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与正义”。事实上,他认为博爱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最多是宗教信仰或者“伪善俱乐部”的教条。
(推荐阅读: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
5、托克维尔的预言
“如果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想想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以及1986年后的台湾,托克维尔在1856年的预言颇足玩味。
他还说了这么些犀利闪亮的话,虽然略带点儿贵族精英感: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